■ 裴 耀 松
1958年11月初,福建省委宣传部从在榕的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抽调部分学生参加采风队,分赴全省各县采集新民歌,包括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流传的红色歌谣。参加的学生必须回原籍,采风活动为期半个月。经中文系推荐,笔者与同届林光沛、上届学长陈家顺名列,三人为组,陈家顺任组长,回清流县开展采风活动。(图为:1950年代清流县城塔寺一景)

地处闽西北的清流县,初冬并未寒气袭人。经县委宣传部安排,城关镇、长校乡为重点采访乡镇,时间若有空余,三人各自回家庭居住地继续搜集整理。带上县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我们首站便到城关各中小学校、部分企业采风。东华乡还在伍乡长的主持下召开座谈、演示会,邀请山歌手,其中还有当年的赤卫队员参加。除记录歌词外,演唱的红色歌谣因不会记录曲调,无法收集。城关是我的出生地,从幼年到青年,生活了二十个春秋。上高中时便从史料得知,早在1931年,清流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便在县城成立。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斗争,贫苦工农民众为支援中央苏区踊跃参加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特别是聆听赤卫队员高唱的红色歌谣,乡音萦绕,方言亲切,让我们这些在异乡求学的青年沉浸在想象的追寻之中。时隔20余年,赤卫队员是当年艰苦斗争的亲历者,红色歌谣的首席演唱者。而大哥大嫂的山歌对唱,有的还是我寒暑假上山砍柴的伙伴,曾在山头歇息时听过你唱我和的歌声,如今又重现在我的耳边。
千年古乡长校乡,位于清流县南部,与连城、长汀、宁化县毗邻,是与县城相距较远的乡之一。北宋年间李氏在此开基创业,我上中学时,班里便有来自长校的李姓同学。采风组早晨从县城出发,坐的是烧木炭发动的汽车,在沙土公路上七拐八弯爬行,抵达时已近午。在李氏大宗祠召开的座谈会上,据介绍,长校乡是个山歌之乡,民情淳朴,“十番锣鼓”名扬。邀请前来的山歌手男女老少都有,其中也有当年的赤卫队员。长校乡原来还是土地革命时期最活跃的山乡,早在1931年便成立乡苏维埃政府,还办过列宁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学生除学习文化外,还有军事知识、站岗放哨、帮助红军家属劳动。在马屋召开的苏区办学评比大会上,荣获红军101团团部授予的“努力教育”横匾奖励。我们还从中了解到,当地贫苦子弟参加红军的热情高,还出现过父送子、妻送夫上前线的动人情景。当时还健在的老红军李宽和、李天光还参加长征,为军师级领导干部。(图为:当年的采风点长校乡李氏大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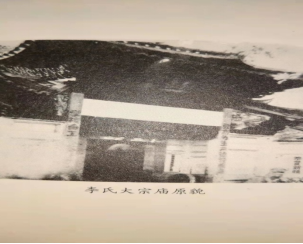
客家地区往往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长校的方言与县城的方言差异太大,在宗祠采风点演唱的歌词,我们三人一句也听不懂。好在有文化站的同志帮忙记录,由于对谱曲一窍不通,只能留下遗憾。从采访收集的红色歌谣汇总看出,长校乡比县城更多,除“韭菜开花一杆芯”等相同的以外,长校乡流传的红色歌谣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在个别歌手的演唱中,我记录了《五更鼓》《少先队上前线》《儿童团歌》《我们胜利了》《革命一定要成功》等。与其他两位相同的还有《妇女觉悟歌》、《剪掉辫子当红军》等10余首。从1958年到1990年,三十多年后,我从清流县编辑出版的内刊《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清流分卷》中发现,包括由原三明市文化局局长郑树钰任主编,编辑出版的内刊《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三明市分卷》入选的清流红色歌谣,印证了长校乡是山歌之乡的美誉。(图为:1990年代初三明市、清流县编辑出版(内刊)的民间文学歌谣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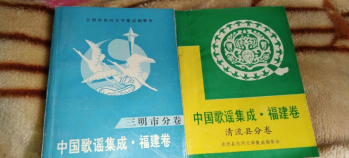
离开长校乡后,我们步行到灵地乡、邓家乡,一路登山越岭,期间还在沿途路过的村落开展收集活动。到了廖武坪,陈家顺回到住家,我俩在他家过夜。次日大早,我和林光沛继续沿九龙溪逆流而上,翻过陡峭的峰角岭,绕了故乡半个县域才抵达县城。林光沛进入嵩口乡,于次日返回嵩溪镇住家。我在城关住家,据亲友介绍,离城二十华里的大路口小星铺,有位赤卫队员会唱革命歌谣,建议前往采访,我不顾旅途辛劳,次日便步行去小星铺,如同旅游,经过的雷公铺、牛屎塘,都是年少时砍柴的必经路。很顺利直接找到赤卫队员的家,因为方言相通,现场歌唱间或补充更改部分歌词,果然有很多收获。
如期返校后,我们将收集整理的新民歌和红色歌谣上交中文系。采风活动是我青年时代第一次回乡参加社会实践,还是学生,不仅享受报销差旅费,重要的还是对故乡有了较深入的感知。心情特别激动,想起年少时在北山与伙伴们拾到不少子弹壳,在“滚来堵”高善亭背砍柴时,曾见到杂草丛生的战壕,南极山破旧的小木屋,后来从史料中得知,原来小木屋是当年红军为保卫县城设立的临时指挥部,北山和高善亭背都有红军作战时留下的遗址。回校不几日,一时冲动,我将搜集到的几首歌谣抄正,投寄到《中国青年报》。没料到1959年3月,竟在该报“向日葵”副刊上发表两首,其中一首《十送》为闽西情歌,另一首红色歌谣为《五更鼓》,歌词是:
一更鼓儿咚,凛凛两北风。
可怜穷苦人,无衣度三冬。
一炉炭火日夜烘。
二更鼓儿敲,提起实心伤。
辛苦赚的钱,豪绅剥削光。
无衣无褥睡光床。
三更鼓儿铛,穷人饿断肠。
镰刀挂上壁,还缺半年粮。
家家户户闹饥荒。
四更鼓儿凄,又来催交捐,
年头到年尾,杂税交不清。
穷人处处受欺凌。
五更鼓唱完,莫说无出路。
工农齐奋起,参加红军去,
铲除劣绅并地主!
四年之后,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永安师范学校任教,多年后又服从分配去厂矿支援办学。每当寒暑假乘汽车在林区公路颠簸,回故乡的路上经过大路口小星铺,一种莫名的思念总会涌上心头。直到1980年代后期大路口小星铺旧貌换新颜,终于抑不住动笔写下《小星铺听歌》,在散发油墨清香的《三明报》报刊版面上,向读者抒发深情的礼赞!回忆往事,重读旧作。(图四:1980年代后期旧貌换新颜的采风点大路口小星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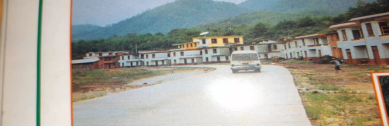
生命的车轮已近半百,时至今日,我依然为自己没有动听的歌喉而深感遗憾。
几次路过离城二十里的小星铺,从苍茫的林海、粉白的吊楼和茵茵的田野,传来阵阵清亮的山歌,心里老想对上一曲以倾吐我的思念,然而只能默诵着难以忘却的歌词。
近三十年了,还在学生时代,我到过小星铺采风。山坡下几栋小茅屋,偎依在丛林的口岸,酷似绿浪中的几叶乌蓬船。那里住着一位善歌的老赤卫队员,记得当时他听说我的来意之后,情不自禁地启开歌声的闸门,用真诚宏亮的方言山歌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杜鹃花开满山红,工农武装烈火熊;铁锤砸烂旧世界,镰刀劈尽千年穷。”尽管时隔二十几度春秋,听当年身临那场血与火洗礼的赤卫队员唱起红色区域的山歌,始终给人所向披靡的勇气。那顿宕跳荡的音调和铿锵的歌词啊!令人遥想当年路隘林深处,歌声,既是猎猎招展的战旗,也是惊心动魂的金鼓齐鸣。我在本子上记下一首首歌词,顶喜欢那首“送郎当红军”。大叔的嗓门粗亮,只好用拟音高唱:“送郎送到大桥头,手扶栏杆见水流;流水长长归大海,万里征途不停留……”倘若歌者是山里的妹子,我猜想那婉转、缠绵的歌声准会惊倒四座。虽说大叔的唱腔并不逼真,听罢十送,可谁也觉得其间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至今我对那首“十送”的歌词还能背诵。当年唱山歌的大叔,几年前已经作古了,他的歌声却永不消逝。每当我路过小星铺,昔日的小茅屋不见了,而粉白的楼房年复一年地增加,那些镶嵌在林带边沿的新宅,兴许便是老赤卫队员后代创业的根基吧!
如今,水泥马路从这里穿过,平平坦坦,北接嵩溪。远近的山峦人工营造的松、杉林风华正茂,山村的风姿流光溢彩。
山里人无论上山或下田,唱山歌的兴致不减当年,你听,“荷——喂——, 日头一出亮鲜鲜,口唱山歌心里甜,昨日扁担弯两头,今朝开起拖拉机……”
那是谁家的妹子?好个甜润的歌喉!歌声飞过林梢,越过田野,飘上公路,令我驻足凝望,思绪驰骋,尽管没有对歌的本事,然而我早把妹子的新歌录在心里了……
(本文作者系永安市客家联谊会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