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 耀 松
平时坚持在生活区域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不少来自故乡的经历和史志的借鉴,发现清流八景诗的由来还有一段佳话。明永乐进士、邑人张永隆担任鲁府纪善(侍读学士)一职时,这年是明永乐乙未年(1415年)四月十七日,鲁王上朝归来的闲暇,在师善堂展开张永隆送来的清流八景图,情不自禁吟哦起来。平时便钟情山水的他面对图景又批览良久,高兴之余,用他的话说“谨奉教命”,便援笔在八景图上书“清流八景”四字。仍然意犹未尽,又另写古诗一章“赐教”:
闻说闽中多胜迹,
景分八韵尚传扬。
白云南极溶溶起,
为雨从龙济八荒。
天际巍峨排翠嶂,
东华一带郁苍苍。
卓立最高名雁塔,
钟声报晓又昏黄。
银蟾昨夜一轮满,
影落龙津潋潋光。
三港清流堪喻道,
半溪残雪渐回阳。
我今为尔一题名,尔宜图画留余香。
鲁王开启清流八景诗的先河,也在岁月的流逝中并不寂寞。响应者首推学士文人,明宣德五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擅长诗赋的邑人赖世隆。如今又以鲁王的古诗为题,创作七律八首回敬。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两位乡贤早已作古,而清流知县陈桂芳主修的《清流县志》,将学者的题记与诗作收录其中,令人欣慰。赖世隆的清流八景分别为:东华翠嶂、南极白云、西桥横笛、北渡孤舟、龙津夜月、雁塔晓钟、半溪残雪、三港清流。(图为清流县旧城新貌)

东华翠嶂
清流东望近蓬莱,
万迭峰峦翠作堆。
林雨初晴眉黛湿,
岭云乍过画屏开。
筠床独对宜清晓,
蜡屣登临印碧台。
愧我棲迟安石志,
少年游赏忆重来。
此后,明嘉靖、清道光、民国的《清流县志》收录《东华翠嶂》的诗作有明成化进士、潮州知府、邑人叶元玉,明礼部尚书、大宗伯、福州人曹学佺,明训导、邑人伍晏,明太学附监、邑人裴汝甲,明崇祯特奏进士、刑部主事邑人伍堣、清乾隆汀州郡守王廷抡,清钦赐大理寺评事、邑人雷可升、清恩贡、邑人伍嘉猷等仕宦、文人15人的七律、五律、七绝、五绝20首。在清流八景诗中占首位。对东华山的形胜展开联想的羽翼和抒发真情。如“风流自笑非安石,也有登山兴来涯”(叶元玉),“竹月粘碎金,松风集鸣杵”(伍晏),“半偈共留今夜胜,十年方遂此游情”(裴汝甲),“堞雉下观真似斗,清溪一线抱城阴”(王廷抡),“拔地千寻林尽翠,去天五尺日犹红”(雷可升),“雨过风敲竹,窗开月照床”(叶纡青),“山深清不寐,饮水有余香”(廖菁我),“暑气山腰退,文心水面宽”(马腾云)等。(图为远眺东华山)

古时东华山有上庵和下庵。上庵在石慈窠口,宋元符年间伍氏族人建伍氏宗祠,亦为东华书院。高拨百仞,陡峻萦行,松竹交翠,如立画屏。现宗祠不存仅留基石和碑刻。下庵即福清寺,旧有观音堂,寺后幸存古树苍劲,绿如华盖,两翼青山,林雨初晴,风光独秀,至今犹存古韵。
南极白云
老人星下耸其峰,
秀色时时云气封。
淡若纱笼金翡翠,
浓如水浸玉芙蓉。
松巢缥缈迷归鹤,
石洞氤氲伴卧龙。
好遂清风天上去,
化作霖雨慰山农。
明隆庆戊辰进士、南京吏部尚书、邑人裴应章有五律《宿南极山》:老兴少年同,寻芳二月中,/桃花红落雨,杨柳绿摇风/泉近琴书润,云深榻几笼/论心贪夜话,不觉晓鸣钟。裴公退休归里,在南极山下结草庐休闲养性,方得论心夜话。明太学、邑人裴汝申、明叶元玉、明经叶宫桃、明经伍嘉猷、明知县陈桂芳、清雷可升等8人的五律、七律、七绝、五绝9首。“地利虽云险,人心未可猜。若非得良牧,剑阁也罹灾”(叶元玉),“羽化何年乘鹤去,岩空终日有云栖”(裴汝申),“晴冷横来多断路,夏峰幻出几奇山”(叶宫桃),“南极山清仙亦喜,白云偶尔驾仙子”(雷可升),“笑指白云深不脱,原来跏坐有神仙”(伍嘉猷),“可提赤手扶明日,下视群山仅一拳”(陈桂芳)。写景抒情、夸张比喻、写实联想、美景如画,对南极山描述恰到好处。(图为南极山汀州亭)

距县城近邻的南极山,后龙枕山,也为朝山。高山群峰,遥望如匹练,延伸南寨为屏嶂关隘。进山有“汀州亭”。腹地有庵和石窟,现为云海寺,百米外另有观音堂,从“石将军”处十米外石窟相传为吴仙人修炼处。道观名曰“白云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于1933年3月底攻打敌卢兴邦占据的县城,南寨山是围城的激战前哨,南极山腹地为指挥所。而今青山延绵,茂林修竹,秀色可餐;远眺新城,高楼林立,曲水东去,盛景如画,已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登山的好去处。
西桥横笛
凤翔桥跨大溪西,
谁倚阑杆把笛吹?
出岫数声疑父老,
据床三弄忆桓伊。
鱼龙起听风生浪,
鸟鹊惊楼月满枝。
一曲吹成太平调,
牧童樵子两忘疲。
西桥历代多为木构屋桥,在县治西,紧邻从明代开始为县衙行政中心。明洪武年间建桥名“凤翔”,夏秋夜人多倚阑吹笛,故有“西桥横笛”一景。赖编修触景生情,“据床三弄忆桓伊”,坐在床上想起东晋喜音乐、善吹笛桓伊刺史,有人竟把依据其笛改编的《梅花三弄》,真切地传递给夜不能寐的乡人。“梅花飘醒三更梦,铁笛吹寒五夜心”“桓伊去后音犹在,许伴骚客月下吟”(邑人伍闽钟),还有情有独钟的“铁笛一声清若许,胡床三弄正怀伊”“莫向瓜洲夸绝技,恐劳江客听忘疲”(清拔贡、邑人廖鸣凤),以及“闲步西桥上,夷犹此暂留。孤城双带水,明月一轮秋”(雷可升),邑人洪径奎的“韵破鸥群鸣获渚,声摇鹤梦醒梧枝”仍然与“夜笛”关联。共计5人的同题七律、五律5首。
凤翔桥在设县治西的宋代便开始兴建,溪流中有玉兔石,“形圆色白,春夏或变青红。成化后间忽坠见底,光莹射日。”清岁贡、邑人伍鼎有七律“疑是当年月窟精,分明化石倚江城”句。清嘉庆年间凤翔桥头有“凤翔阁”,桥尾西山“文昌阁”。数百年来,凤翔桥毁于水或火,或于寇,仅万历记载的五十年间,毁与建便达三次。无桥年间便以浮桥代步,志书记载的《建造西门浮桥碑记》便可明证。民国时期长年两桥全无,出行甚为不便,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简易木板桥,后才重建西门大桥。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建的凤翔大桥,石拱卷结构上部空腹,下部为石台档,经历多次山洪考验坚实牢固。如今处县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盛景繁华。倘若静夜,凭栏注视水面,流光溢彩;闪烁的楼宇倒影,似在天宫。真个是,西桥横笛今犹在,一曲心中乐太平。(图为上世纪70年代的西门桥)

北渡孤舟
溪头宿雨涨新波,
一棹随鸥拥绿蓑。
泛泛柳阴轻似叶,
摇摇天际小如梭。
巨川用汝相期切,
野水无人感兴多。
闲却清溪好风月,
暂烦酌酒听渔歌。
清拔贡、唐县知县、邑人廖泉以同题七律,描述的场景是“彼岸两山才咫尺,扁舟一叶道将迎”。“似画溪深崖断处,添描野渡景纵横。”清岁贡、邑人叶锡辂的同题五律、雷可升的七绝,却是白描,“旅客关心处,桑乾回首时”。“沙头人立马,独唤隔溪湄。”“邑枕屏山晚翠溪,绿杨钭蚋白沙洲。行人欲渡心逾急,坐看清溪月乱流。”而赖编修的“北渡孤舟”,是一幅水墨画:孤舟轻似叶、小如梭,在涨新波的溪流中,划着浆,伴随鸥鸟和绿岸驶去。(图为上世纪70年代的北渡孤舟)

北渡孤舟固然可以入画,历史上的物流主要依靠肩挑手推,从坊廊里大基头、供坊等地挑运的农副产品必须绕道东门和西门进城,倘若两地的桥梁损毁便成绝路。在北门建造浮桥,并断断续续延至清流解放初期。仅有清乾隆年间的罗知县主张复古,认为北门不宜建浮桥,呈请恢复设渡以济,获准恢复北渡孤舟。这也是一厢情愿,毕竟现实与画图相去甚远。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原址建造铁索桥,仅通行人和板车,不几年遭山洪冲毁。从此古时的北宸门既无浮桥也无舟渡,自从蓄为平湖之后,舟楫仍至机动船只往来,又添一道新景。
龙津夜月
月夜登桥疑步蟾,
水晶宫里见婵娟。
山高错讶玉盘小,
波静方知银镜圆。
对影吟诗惭李白,
问天把酒忆坡仙。
清溪此景谁争得,
独载光辉满钓船。
清乾隆汀州郡守王迁抡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对清流八景情有独钟,不仅撰写《重建龙津桥记》,还有同题七律,“日荡流波飞电彩,波天皓月散珠光。”“歌声傍火来渔浦,笛韵因风起凤翔。”雷可升的排律记叙嘉庆五年遭冯夷烧毁的“凤翔龙津无片瓦”,吟诵龙邑侯为重建龙津桥。“浃辰齐举势穹窿”。恢复长虹后,“扶老携幼履道坦,顿觉秋水剪双瞳。”从此“吾侪乃复得过此,月夜吹笛惊潜龙。”清拔贡和顺知县、邑人余光超的同题七律,“龙津东去水泱泱,秋夜怀人一片霜。鹅髻峰高低雁塔,蛟宫夜静吐珠光。”直至民国仕人赖鸿基的七律,又有“出岫闲云浮玉宇,哺雌归鸟匝林窝”。还有文人赖以传七律二首,“山城谁最饶风景,潭影山光此处多。”“一抹残阳留古堞,数声柔情逐轻波。”
自宋置县以后,城东便是郡邑咽喉,始无桥,以舟渡。最初建石墩六、飞屋四十间,匾曰:“龙津”。屡建屡毁,直至民国为木架构平板桥。解放后多次重修,其中有梁架为钢板,可通限吨位汽车的公路桥。1994年5月2日遭特大山洪冲毁,仅剩桥墩。清流县委、县人民政府多方筹集资金,全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于1995年9月重建竣工。为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高程增加4.6米,四墩两面,钢混拱桥,蔚为壮观。大凡形胜以景寄情,赖编修的“月夜登桥疑步蟾,水晶宫里见婵娟”似乎又再现了。倘若静夜,明月一轮秋的时分,桥上凭栏的市民,也是在共享“两轮秋月共团园”的美景吧!(图为新建龙津桥)

雁塔晓钟
早鸡声里忽钟鸣,
唤起当年古寺情。
林外月钭敲正急,
山中霜冷听偏清。
客船夜泊愁惊梦,
官署晨衙喜报晴。
我有新诗寄僧壁,
纱笼却笑宋人庚。
还是要提起赖世隆的“唤起当年古寺情”,东华山对他来说是少年“忆重来”,仅仅游赏而已,而雁塔是深情的想念。当年他在这里读书求学起步,也如同朝的南京吏部尚书裴应章,在温郊上阳山“七易寒暑”,对赖仁敷恩师一往情深。而赖世隆为明宣德进士,直接进入翰林院任编修,而且文才出众。他协助朝廷镇压邓茂七农民起义出过力,却因得罪当朝权贵而被冷落,从此止步。清流县在改革开放后,西山坪背是开发区,在清理野地荒坟中挖掘出赖编修的墓葬,笔者听参与者相告,仅发现一顶锈迹可辨的“官帽”。明嘉靖《清流县志》“坟墓”记载在西山坪背。而仅从清流三部《县志》中发现,赖编修的诗文数量都可夺魁,文章千古事,后人自有评。
雁塔在县城内的马家山,也是唯一的制高点。早在宋淳佑五年(1245年)便建万寿寺,多次毁于寇与火而重建和更名,早年并无塔。张永隆借用唐代西安的雁塔入诗,而到了清代已有塔,雷可升的五言排律有“雁塔耸东方,巍然列入景。东望碧潭深,西顾青山岭。”“昔忆慈恩寺,题名待红杏。”(清钦赐大理寺评事,也在此求过学,并在这里接受题名优贡,红杏出墙)。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知县阮公创始翟延策继之,并有“雁塔铭”,邑人裴应章为之记。说的是在此地还建有七层砖木塔,曾题“雄凌五岳,秀孕二元”八字,篆刻于门楣。清末以前,上述建筑均成遗址,民国后重建两层楼阁,内供奉五谷真仙,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损毁。(图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雁塔晓钟)

半溪残雪
江南点雪值千金,
今喜溪头一尺深。
怪石冰融寒鹭疲,
小桥日上玉虹沉。
渐看草色回平野,
未放梅香出远林。
乘胜何须移夜棹,
蹇驴随处探春吟。
清岁贡、邑人叶锡辂同题五律句,“天花飞不歇,经岁乱滩头。冷浸孤山月,光回剡曲舟。”邑人廖泉七律句,“白石中流雪复凌,皎然历乱照澄凝。桥横策蹇诗怀冷,鹤立窥鱼足迹明。”邑廪生廖佳玫的七律有“遥从落月抛残照,解遍凝冰冻少留。是处袁安眠不稳,闲吟驴背出沧洲,”伍嘉猷七绝:“岂真人尽玉山来,仿佛溪南石几堆。想是天花思结子,半留清白作胚胎。”
半溪在县东北坊郭里,也即现今为白石桥下溪段。其源流出自永德里(嵩溪青溪),水合白石桥溪,汇入大溪。因为半溪多白石错落,远望如未消融的白雪,才有“半溪残雪”一景。八百多年后,白石桥地名还在乡人中叫唤,也在当地史志上记载,如今却从一个荒野之地变为村民的居住点,而溪中的白石,文人雅士诗中的“点香”“天花”“流雪”“玉山”全都无影无踪。连同小桥附近的山丘,在那个时代被视为风水宝地,包括元朝的总管、明代三个知县,还有教谕、训导、处士等,全都争着在那里安息,也都随着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消失了。(图为上世纪70年代白石桥溪)

三港清流
众流合处水平沙,
浅碧粼粼望眼赊。
夹岸桃花迷远近,
傍桥梅影见横斜。
四时鱼美多渔钓,
百里滩连少客艖。
最是深夜堪玩处,
一溪渔火映山家。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清流是水的故乡,县城还是三溪合流之地。明嘉靖《清流县志》“三港溪”:在县南郊。第一港出于地名大基头,流至小溪头,入于大溪。第二港出自地名青溪,流于上堡白石桥至溪口,入于大溪。第三港出自宁化界黄地铺,流入吴地铺,出三港桥,入于大溪。会三溪合流,澄清如练,故有八景中的“三港清流”。清道光县志又作补充:“中有符石,长丈许,相传有蛟潜伏,民居常有崩震之患。邑人伍姓者有道术,刻符篆于石,蛟患遂息。”
前者为实,后者传说。或许古代文人墨客少有身临其境,未曾诗兴发作。赖编修的“夹岸桃花”、“傍桥梅影”,还有“深夜堪玩”、“渔火映山”,也与其失之交臂。作为今人,如笔者三处流域也曾留下足迹,并非一日之兴,既惊叹其澄碧清流,也曾结伴垂钓,收获满满,乐而忘归。大自然的天造地设,让后人感恩不尽,留下的山水美不胜收。可惜多因陶醉未醒,未能留下寄情的诗文。
清流八景诗,在历代编修的《清流县志》除明崇祯、清康熙编修的缺失外,均有收录。也有未收入的散落在民间族谱中。如福建清流《安定郡伍氏族谱》中便有信房廿三世一翰公、廿四世闽毓公的《雁塔晓钟》、晋阳公的《半溪残雪》等,犹以东华山的诗赋最多。《旧志》对山川、形胜的风景定位,有一段见解:“盖景原无定,唯情则生,随时生情,则随地皆景。安得执郡邑之某山为某景,某水又为某景?迂甚矣!”不过,无论为景还是为情所生的风景名胜,还要数清流郊区的《灞涌金莲》。清道光的《清流县志》载“灞涌岩,清泉怪石,茂林修竹。唐武德三年,僧云谷来曹溪游,居此山中。初无水,传有圣僧定光,一日至此,飞锡凌空,七日复还,合竹引之,始有泉涌。是夜风雷大作,雨滂沱,山僧惊避,迟明视之,庵推出于谷口,其下飞瀑数丈,如珠帘玉箸,至今莫寻其源。”唐武德三年(617年)也即唐高祖(李渊)立国之初,距今已1306年了,现今这一佳境,依然引人入胜,真个是“唯情则生,随时生情”。叶元玉的七律《灞涌岩》,“金莲山寺万松阴,流水花开自古今。几发青螺撑佛顶,半岩秋月印禅心。”“满天风雨龙归洞,入座笙歌鸟隔林。骏马神鹰无觅处,一声鸡犬在云深。”裴应章为金莲寺的题联为:“泉声夜夜三春雨,山气时时五色云。”王廷抡的七律《灞涌金莲》,“涧底千章武德树,崖边一曲锡飞湍。”邑人邓煊的五律“凭栏还北顾,紫气望中浮。”直到民国时期仕宦王琼的《古八景联》:“踏雪以访金莲行径翠嶂东华遥听晓钟鸣雁塔,驾孤舟而横玉笛吹得云开南极高悬朗月映龙津”。将“灞涌金莲”也列入清流八景之一,足见其自然形胜、人文历史的厚重。“灞涌金莲”诗联总计达20余首,超过“东华翠嶂”,为首位。(图为灞涌金莲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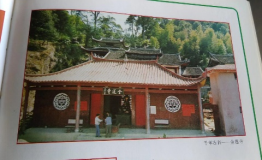
随着清流县城的发展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提出建设“内陆鼓浪屿”的岁月里,几十年来自然和人文景观彩盛花繁;深入探寻千年古县文化的积淀,获得新的发现;保护好古代山川的形胜之美,后代子孙任重而道远。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志于家乡繁荣昌盛的志士文人,在弘扬客家文化中既传承又创新,定能创作出更多的新诗章,放声歌吟清流的如画美景!(图为清流县城夜景)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永安市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