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 衍 森
三元是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它开门见山,四面青山环抱,绿水长流,而我的老家便在红印山下,正是三元城关的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城关百货所在地。对岸是三明南站,背后与绵延的虾山相望。你也许会惊奇地问道,哪里是“红印山”啊,应该是“文笔山”吧!我的回答是,答案都没有错,因为二者都是同一山脉:就整座山脉来说,就叫文笔山。但文笔山明显分两个层次:从山下到文笔顶,统称文笔山;而从新市中路路面到原海关和绿都大厦以上一围山丘,东从“三元圆通堂”开始,南绕省安小区,遥至原标准件厂(白石岭头)一带,便是人们习惯上称为的“红印山”了,现在的三元区城关街道红印山社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文笔山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里便不作介绍,现就说说红印山,我的老家就曾在它的脚下,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它是个很有故事的地方。

一、地名记忆,“杉联”之谜
三元古时人们称为“杉联”,明朝是隶属沙县管辖二十二都的一个山村。那么,“杉联”的名称是从何而来的呢?近年,随着全国优秀民俗文化发掘、发展和弘扬,古老的《三元龙船歌》也荣耀地登上了市级优秀非遗榜,并成了人们经常传唱的歌谣之一;那高亢、雄浑《三元龙船歌》对三明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非夸大其词:2014年2月24日那天,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节目组专程来到三元,并在美丽如画的旅游胜地月亮湾,拍摄了优美的《龙船歌》演唱情景及气势磅礴的龙船竞渡画面,从而将此项市级非遗项目推到了全国民众眼前,让全国文明城、卫生城三明又增添了新的亮色。我之所以要写这些,目的就是要引出《三元龙船歌》的第一句歌词:“后门杉树几千年”这句强音。据谱志记载,旧时三元,远近乡邻都称之为“杉联”。究其原因就是红印山一带,古时几千年来这里都是一片郁郁葱葱,绿波荡漾,野兽出没,不见天日的杉树林,故周边乡里都亲切叫它为“杉联”,意为“杉树的海洋”。我脑海里至今还铭记着母亲告诉我的一句民谣:“吃不完台湾的米,用不完杉联的材”,便是三元当年杉林云海般的写照。也许你要追问,那“红印山”名称又何从来呢?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红印山地面是淡红色的粘土,杉树再多再密,部分土色总会裸露出来,每年时值春天阴雨霏霏之际,人们登山上路,常因红泥路滑,不免摔跤,屁股不免粘上一对红红印迹,所以人们便亲切称它为红印山。如果您想验证一下,只须上三明林校走走,看看上山小路裸露土地的底色,便有答案了。缘此故事,“后门杉树几千年”的歌声,世代萦绕在三元人的脑海里,虽然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

二、乡贤乡规,绿水青山
也许你要问,旧时三元,和全国一样,人们煮饭沐浴取热都要用到柴火类的燃料啊,红印山怎么能保得住千年的“杉联”不败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把红印山一脉,看成哺育自己安身立家的神山,容不得乡民有半点的侵害和破坏。更重要的是,它有代代相承的乡贤和近似苛刻育林护林的乡规使然。那么几千年来,当地村民需要的燃料是怎么获取的呢?是的,三元一带并无煤等燃料资源,而当时能利用电能更是天方夜谭。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对于植被葳蕤、绿荫丛生的三元来说,可用于烧火取暖、煮食烧菜之类燃料,灌木杂草类等多得数不胜数,根本用不着去砍伐那些要保护的杉、松、樟、楮等名贵树种,那些满地爬行、四处乱长,特别是拦路的荆棘藤蔓等都要劈除清理,而其中灌木类作为燃料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然,要长期保护杉联,仅靠道德上的说教传承是不够的,那些青史留名的护林名贤及其苛刻的护林乡规才是其最关键的原因。
下面给大家说说谱史留名的护林名贤及其苛刻的护林乡规。说起三元的护林乡贤,举不胜举,其中头一名的便是鼎鼎大名的邓启棠了,乡亲们都亲切称他为三元护林英雄。邓启棠,明朝人,字尧章,三元城关人,是个太学生。因为对后门山蓄树有功,蜚声闽省内外,当时福州府闽学教谕李印英,听到他的事迹后,不禁深为感动,肃然起敬,便以闽府教谕的名义,赠送了一块匾额给他,上书“拟阴甘棠”四个金字,以褒誉他不懈为乡护林的功德。“拟阴”二字,就是保护山林的意思。而“甘棠”的意思就是指“护林的及时雨、保护伞”的深意。为什么他的功勋最大、最能感动乡民呢?原因在于他不仅以护山为己任,更重要的是他主持制定了近似苛刻的《护林乡规》,对长期保护山林起了定山神针作用:凡是触犯乡规故意上山伐木者,责令其须“桶盂印粿”,并分发到全乡各家各户。这个规定是很严酷的,要知道,一个所谓“桶盂印粿”至少要用二十多斤粳米。而以当时三元人口计,全乡应该不少于两千家。而如犯此乡规者,其家境即使是富裕者,也难免倾家荡产,更不用说贫困之家了。更令人震惊的一项举措是,为了验证这项乡规的严肃性,令行禁止,邓启棠决定假戏真做,故意叫自己的侄儿上山伐薪,并暗中叫人巡山逮着,然后让其当众认错,接受“桶盂印粿”的处罚,使他侄儿蒙受倾家荡产境地。目睹此乡规之严厉后,广大的乡民自然深受震动与感动,其后乡里便无人敢于损坏山林了,红印山森林资源得以保护下来。
当然,俗话说,独木不成林、单人不成气候,红印山的杉树千年来郁郁葱葱,传为佳话并非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世世代代护林贤人志士不懈维护的功劳,更是一代代乡民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结晶。
三、民国劫难,鬼哭狼嚎
可惜,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禽兽出没的杉林,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毁灭性的劫难。民国初年,贪婪而残暴的沙县县长王邵璧以筹办“保卫团”为名,葬送了千年的“杉联”人间仙境。人们常说红印山是三元的母亲山,沙溪河是三元的母亲河。可是,这位贪婪成性的豺狼县长,竟以筹办保卫团为名,滥伐沙溪两岸的山林,红印山森林亦在滥伐之列。成排成排的杉木一眨眼便被滥伐殆尽。而广大的乡民,迫于穷凶极恶的统治者的淫威,只能眼巴巴看着这群坏蛋的胡作非为,敢怒不敢言。最终的结果是,山体狼藉,哀鸿遍野,成堆成堆的杉木都被拖运到沙溪河岸,进而被捆扎成串串木排,顺流运到南平、福州等地贩卖,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几千年来翡翠般的杉林树海就这样消失了,千古佳话的“杉联”一词只留存在古老的《龙船歌》了。
雪上加霜的是,抗战时期,南永公路的开通。它的开通对抗日战争与三元的开发来说是件很有意义的大事。但是,那些劣绅土豪却利用机会,损公肥己,不仅砍杉木、松木等,连竹类也不放过。能卖的便卖,能烧的便烧,更没人敢出面主持封山育林之事了。从此,红印山便成为骇人听闻的“荒山野冢”了。我们这一辈的人都知道,解放初期,作为孩童时期的我们,大人是不许我们上红印山的:这里已变成一片荆棘丛生,荒冢密布的地方,世代相传的神山林海,变成了小孩不敢去的“鬼山”。当然,解放后此处又发生了山乡巨变,随着宽广的柏油大道新市路的开通,路边绿都大厦、海关大楼和三明市眼科医院等楼盘和红印山路、文笔路文化场所的修建,现今已是焕然一新,今非昔比了。
四、书香圣地,文化摇篮
上面讲的是红印山正面山体的沧桑巨变,以下说说红印山东部的变化。东部区域即现今的红印山路和右拐的文笔路、富文一路和富文二路等一片区域。这里从古至今都是三元的书香圣地,文化摇篮。历史悠久的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就在红印山脚下,它开启了三元现代教育的先河,世界著名的学者陈景润就曾在此地度过初中学习生涯,为了纪念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原来的三明市实验小学,改名为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沿着红印山路往上走几百米,往右拐爬一段小坡,直至富文一路口,现名文笔路,这一带山丘就是旧时红印山一脉,抗日时期南迁的“江苏学院”旧址便曾在这里安身立命,给此处山水又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因《三明文史》已有专文介绍)。由富文路口,再往上行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正前方是鼎鼎大名的三明林校,是一所培养各类工匠的摇篮;它的门口右边,是三明市歌舞团的所在地,莺歌燕舞之声时常萦绕之地;往下便到了富文一路左转至富文路二路,这个区域更是云蒸霞蔚之地,因为三元有个著名的书院就在此处,现在三明一中办公室就在这里。这个书院叫“庆龟书院”,也有人称之为“圣者殿”,更多的人称它为“庆龟祠堂”,因为它兼有书生读书和邓氏宗族祭祀两大功能。据《延平府志》记载,宋嘉定4年(1210年)建。因地点位于红印山下,地处幽静,历作书斋。明宣德乙卯科举人,萍乡县知县邓福等人,曾在此读书修业。其原宅基面阔5间,深三进。前坪外有泮池,东侧有橱间宿舍,门坊、下厅、边厢、天井,上三厅。上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三明一中的前身三元县初级中学在此开辟新校园,揭开了庆龟书院新的一页。在三明一中2015年校庆时编写的《三明一中建校七十周年的画册》中,留有这么几行诗句最动人心弦:“春日火红的木棉,仲秋金黄的银杏,见证你的荣光,足迹深深,一路走向辉煌。”短短的几行诗句,见证了此地的岁月沧桑,文脉的芬芳。千年以来的“杉联”,又增添了木绵、银杏等名贵树种色彩的芳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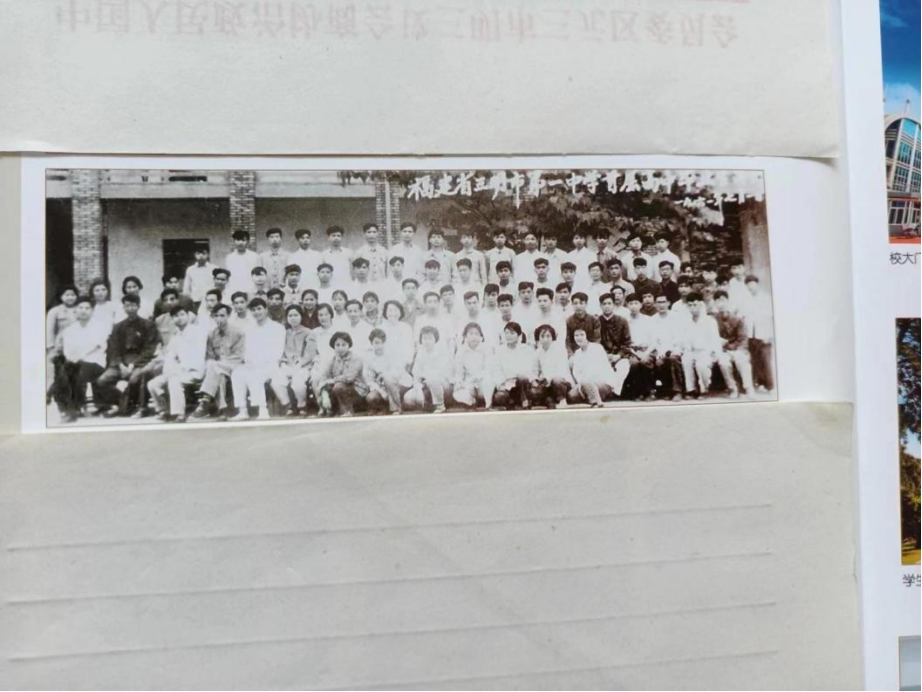
其后,三明林校、技工学校和职业学校亦先后在周边开办,形成了一道浓浓的文化氛围区域。综上所述,红印山是一处值得我们记忆收藏的地方,我们不能忘记。
(本文作者系市政协文史研究员、三明一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