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烩 阿慧
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甜蜜的世界,走进了三明人的视线。那一片片酥脆可口的饼干,那一块块松软香甜的花生牛轧糖,那一杯杯香醇浓郁的咖啡茶,更有那一瓶瓶清凉解暑的咸汽水,在不少50、60、70后中老年人心中,留下了那个年代舌尖上的享受,贯穿了三明好几代人成长经历的美好滋味,仍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心间,在生活的延续中口口相传着。(图为河对岸的建筑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明食品厂)

10多年前,在市区林委上虎头山山路边的洼地,认识了吴泉华的老人,高个、粗犷,有着客家人的豪爽。他在那片坡地上盖了两层简易的小木楼,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还有四季常青的果蔬和一条大狗。后来慢慢熟知了,才晓得这老爷子守着这一片“国土”过着滋润的生活,自家不仅吃着自己种的鸡鸭果蔬,每周还能杀两只鸡鸭送给两个女儿。还得知他是1958年就来到三明的建设者,当时他才从梅州考进漳州师范一个多月,因后妈不肯寄生活费而窘迫的他,一听说三线建设招工,就报名参加来到了三明。其时工业局的曹局长看到这孩子机灵,又会写一手毛笔字,就把他要到工业局当通信员。他跟了曹局长一年多后,恰逢困难时期,老觉得18元工资太少,就嚷着要去工厂当工人。曹局长问他想到哪儿去,他打着小算盘,说去食品厂。正因为是工业局通讯员的身份打探到城区三明食品厂刚从上海迁来,福利待遇好,身边的食物随便吃。曹局长一个电话,他就进了食品厂。老吴说到了食品厂真享福啊,汽水、饴糖、饼干任工人吃。食品厂养了他一年,他又不想干了,就因为还是学徒工,18元工资太少了。他又找了曹局长,曹局长说,你留在我身边有前途,你怎么就不想干呢?他说,我不就想赚钱吗?曹局长应他的要求,又让他去了市政公司。市政干活,整天刨石挖土铺马路,钱是多了不少,可劳动强度太大了,他干了几个月渐渐吃不消了。于是他又找了曹局长。又是一个电话,他到外贸报到了。从那里起,他留在了外贸……
传说中的老曹,是92岁的离休老干部曹忠泉,夫妇二人至今依然健康地生活在列东红岩新村20幢的二轻老工房3楼。老吴遇上了好领导,在那特定的年代,可以频频跳槽。而1953年就走进上海三星糖果厂的女工马春云,这位来自浙江省余姚县临山的山村贫苦姑娘,她和进厂后的工友、后来结为夫妻的广东潮阳县棉城的贫苦农民肖燕鸣,一生一世的命运,都与三明食品厂紧紧相连着。
像马春云夫妇这样在建国初期就进三星糖果厂的工人,在三明城区已很难寻找了。只有那一代人,还很清楚地记得:1932年,在黑云笼罩的上海,有位牙医把他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徒弟杨吉明,于是这对小夫妻开始生活自立。他们毅然在中华路小北门的简陋小房,经营起咖啡茶的制造和销售生意。这便是至今闻名的“鹅牌咖啡茶”的起源,马春云这一线女工就听说杨吉明老板很厉害,压根就没能认识杨老板是什么样的面孔。仅仅是听说,1937年,这个咖啡小作坊的杨老板扩大经营范围,把小作坊变为以咖啡茶为主要产品的“三星糖果厂”,至1944年又一厂变三厂,职工由20多人猛增到300多人,年产糖果500多吨。在一片“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三星糖果厂又得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图为参加厂房建设的工人们)

马春云一直在三星糖果厂干到1956年公私合营,才在会场远远地看到杨老板。但她感受的到,在三星打工很不错,路上遇到老乡,听说是生产“三星糖果”和“鹅牌咖啡茶”的工人都觉得很体面。
今年已经83岁的马春云,说起老厂的历史,依然有一种五味俱全的情感,时而激昂,时而哽咽。1960年,这个历史悠久的三星糖果厂,为支援山区建设,迁来三明,马春云和工友肖燕鸣义无反顾地离开繁华的都市,落户在新兴工业基地。
1960年3月,三星糖果厂落户在如今列东东新一路(高岩社区)的一片梯田中。100多名工人抵达三明后,他们披荆斩棘,挑土开荒,秉持当年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他们在搭建简易的生活窝棚后,就积极参与厂房建设,挑土、搬砖、推板车、拌沙浆、砌墙,抢运物资和设备。老马说,那时节人心真的齐啊,都不要领导动员,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就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老实憨厚的肖燕鸣,待小他11岁的马春云像亲妹妹一样,处处呵护着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1961年,新建成的三明食品厂便开始投入生产,白手起家,当年即为国家盈利。他们生产的月饼、汽水、牛轧糖、棒棒冰、乳儿糕给老三明建设者带来了甜蜜的回忆。也就在那一年,马春云和肖燕鸣走进婚姻的殿堂,有了甜蜜生活的开始。(图为在梯田中建成的新厂房)

1937年出生的马春云,16岁进三星糖果厂做工,是苦罐子里泡大的。三星糖果厂公私合营后,她就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尤其是迁厂到三明后,她就以厂为荣、以厂为家。熬糖,是食品厂一般男同志也难以胜任的工种,她知难而上,是三明三星糖果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熬糖女工。而肖燕鸣也是熬糖工人,一起熬出了“甜蜜蜜”;没想到的是,后来他们的大儿子进厂,也是一名合格的熬糖工人。马春云从熬糖到包装,几个车间都呆过。只要哪个车间需要,她二话不说就听从分配。1963年,为了改善员工的生活,马春云还带头到养猪场养猪,她总是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却从来不说苦和累。1962年,她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五好青年;1963年出席省工代会;1964年被评为厂学习毛主席著作单项标兵;1965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1966年上半年被评为厂单项能手。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很多工人脱产“造反”闹革命,马春云却与老公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因此,马春云在车间受到了造反派的围攻谩骂,轰出会场,甚至拳头、铁棒等围殴恐吓。马春云一门心思为“抓革命,促生产”努力。为此,“食品厂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在1968年10月15日还对马春云在岗位上的“促生产”做“充分的肯定”。(图为当时“造反派”对马春云的“鉴定”)

马春云和肖燕鸣的新生活也跟新厂一样,两个儿子先后出生;那叫蒸蒸日上,一天比一天好。三明食品厂至1965年,年平均为国家盈利33.92万元。十年内乱时期,尽管生产十分艰难,年均利润也达21万多元。(图为上世纪60年代三明食品厂工人休息时品尝自己生产的汽水)

1960年底,凝聚了百名工人的智慧和汗水的食品厂糖果车间、饼干车间、咖啡茶车间的3座厂房拔地而起。老工人感叹:那时没有竣工仪式、更没有开工典礼。我们一伙工友围绕厂房门前席地而坐,喝着自己生产出的第一批咸汽水,不断碰瓶“干杯”,用最简单的方式欢庆工厂落成,真的惬意啊!
当时工厂搬迁到三明那时节,根本没有设置搬运的工种。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到员工的头上。马春云说,当时食品厂的原料仓库设在厂房三楼,每周都有原料源源不断地进厂。其中最轻的面粉一袋40斤,最重的白糖200多斤一包。男工扛,像马春云这样干过苦力的女工也一样扛。(图为上世纪60年代三明食品厂工人正在制作月饼)

厂房建成后,第一个投产的车间就是饼干车间。老马记得当时是饼干车间主任陈辉勇挑重担,到上海食品机器厂商谈交换饼干设备事宜。那时节,三元当地生产的饼干的都是一些小作坊,饼干制作工艺简单,没有发酵,没有添加麦芽糖,入口像地瓜干,嚼不烂、咬不脆,更谈不上口感了。新厂需要一套饼干自动化设备,但没有采购设备的资金,怎么办?当年25岁的陈辉,脑子活络,想出了办法。他得知上海食品机器厂缺少松木,而三明森林资源丰富,多的就是松木。松木在上海人眼里稀缺珍贵,而三明山里人日常当柴火烧饭。双方很快达成协议:一手交松木,一手交机器。几番周折后,搅拌机、成型机、烘炉机……一套崭新的饼干自动化机器终于出现在员工面前。这一套流水线的生产,不仅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还为市民带来了新食品。虽然没有漂亮的包装盒,没有精致的分装袋,更没有复杂的包装工艺。饼干烧烤后,在秤上一称,一个大铁皮盒,30斤一箱,就送到商场销售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饥荒,人们皆因吃不饱,缺乏维生素B,得了浮肿病。当时的三明市商业局正为此事发愁,看到市面上出现好吃的饼干后,商业部门将目标锁定三明食品厂。令陈辉他们没想到的是,商业局领导找到厂里,要求他们生产制作糠饼,化解当时的浮肿危机。(图为1964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在三明食品厂门口留影)

糠饼不能说不是“奇葩”食品,当时就因为吃不饱才得浮肿,如果政府有充足的面粉和白糖制作饼干供应市民,还会有人挨饿吗?政府为解决饥饿产生的浮肿,医生开出的米糠,还不是随意开。米糠怎么下咽?如若简单制作成糠饼,不仅硬、没味道,虽然能更好地填充肚皮,一点口感都没有,浮肿的患者怎么吃?为了让糠饼口感能诱惑浮肿患者的食欲,食品厂的老师傅们终于想到了将麦芽糖和厂里生产的饼干渣子一并加进糠饼中,既能增加弹性还能添加甜味。
糠饼一经推出,商业局的领导致谢,水肿病患者感恩,连为浮肿病开“糠饼”处方的医生都想亲口尝一尝。
当年,三明食品厂主打产品鹅牌桔子粉、三星牌花生蛋白糖畅销全国各地,还有其中鹅牌咖啡茶悄悄进入三明的商场,慢慢地走向全国和港澳的寻常百姓人家。
在那个年代,咖啡茶绝对算得上稀罕物。咖啡茶的制作,需要经过磨粉、成型、包装等多道工序,男女工配合才能完成。在咖啡茶制作中,男工主要负责炒熟咖啡豆、咖啡豆磨粉及白糖揉粉等需要体力的工作,这其中白糖揉粉步骤尤为关键。糖粉揉搓约需10分钟,揉搓好的糖粉要做到捏起来是一团,但一放开就散了,这才合格,所以很考验工人的技巧。

咖啡茶剩下的成型、包装等制作工序则由女工完成,当时食品厂的热销产品鹅牌咖啡茶,只有6名女工与男工搭配。马春云还清楚地记着咖啡茶的制作大家都一丝不苟,不是男女搭配,有说有笑,干活不累。上海厂对工人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在工作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更不能调侃说笑。女工们在成型工序中,她们需将揉搓完的糖粉放入模子里抹平,扫去多余的糖粉,再在中间打个洞,用一根木棒将咖啡粉拨到洞里,接着用盖子压实成长方形模块,一块咖啡茶就制作好了。这一切看似简单,不需要多大的气力,但要完成这精细的活,必须心灵手巧还得敏捷。压好的咖啡茶进入了烤箱,抽干多余水分后,再用蜡纸包装,放入硬盒里,就可以进入市场销售了。那时节虽然没有质监和食品卫生部门的监管,他们却从来没出过纰漏,因为好人就在身边。(图为马春云出席省工会三明代表留影)

当时,新上市的鹅牌咖啡茶香浓醇厚、提神醒脑,一上市就获得消费者的好评,至今老三明建设者在茶余饭后依然回忆着当年聚会时的饮品。
从上海来的工人、干部和后来陆陆续续进厂的员工,都有着一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总有一种无形的鞭策,鼓动着他们辛勤劳作、点滴努力、多做奉献。并以笃定的诚信经营,促使员工们严于律己,以地道的选材,不断捕获消费者的味蕾。(图为工人们在生产糕点)

文革中的1973年4月,马春云离开了食品厂,作为当时时髦的“工宣队”进驻三明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领导起文艺工作者。文革后,文宣队改制为三明市越剧团,马春云任团长、支部书记;1987年剧团撤消后,马春云任三明市文化招待所所长直至退休。她在食品厂兴盛时期离开,离开老厂,她的心还是跟老厂紧紧相连,不仅仅是因为老伴和儿子还在老厂。到后来眼看着食品厂慢慢地退出三明历史舞台,真的是有心治厂,无力回天。
据新闻报道: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明食品厂全体职工发挥了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使生产不断发展,生产规模扩大,总投资由七八年前的240万元增加到450万元,1984年建成投产一座2000平方米的饼干大楼和一座6840平方米的糖果大楼,从而开辟了本厂食品生产的灿烂前景,生产糖果、饮料、面制品三大类130多个品种,其中鹅牌咖啡茶、花生旦白糖、巧克力酥心糖、威化饼干和桔子粉为省优产品,产品畅销全国17个省400多个县市,并有中华猕猴桃糖等5种产品打入香港市场。8年来,平均利润83.86万元,相当于迁厂前17年年平均利润的1.62倍。1984年,厂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以改革精神抓企业整顿,使生产和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实现了两位数三同步,荣获三明市1984年度工贸工作先进单位和省经委命名的文明单位的光荣称号。1985年更上一层楼,完成产值利润又比1984年同期分别增长46,92%,利润增长一倍多。
在大好形势下,隐患和危机已经悄然潜入了三明食品厂。这一期间,肖燕鸣早已退休。他和马春云的大儿子接班进入食品厂熬糖。老马夫妻还暗自庆幸儿子能顺利接班,接续上海的食品名牌在三明发扬光大。
三明食品厂从1960年落地三明,生产的各类糖果和糕点走入省内外寻常百姓家,给人们带来了“三明的味道”。没想到在改革开放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更由于原材料白砂糖的政策因素,造成食品生产的巨额亏损。(马春云退休后的一家子)

在老马的儿子进厂后,那年景是一年不如一年,直至后来被上市后的三明农药厂兼并,熬糖的儿子还进了农药厂上班,不再为市民生产美味食品了。当然,农药厂其时还兼并了三明啤酒厂、三明制药厂,人们不再津津乐道。老马的儿子小肖成了老肖师傅,后来在“三农”又一次下岗,怎么也想不明白,才人到中年,就“买断”了呢?不只是老马的儿子想不通,老马夫妇更想不通,改革,怎么就把好端端的国营企业改进了死胡同?当年自力更生,靠大家的力量盖起了厂房,用工人们的双肩扛进了机器设备,不断生产出了市民喜爱的食品。都改革开放了,反而将工厂和工人的出路都给封堵了?时代变了,通途也改变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就在1995年食品厂大门口的厂牌被摘下后,老马和好多个老工人哭不出声,那心痛是没有词语好表达的。他们从1960年跟随三星食品厂随迁三明35年,早已被福建口音所改变:怎么会“姐样紫”呢?现实就是这样子,凤凰涅槃,很多新人有了新机遇,走上了新路。但以一穷二白双手从原野中托起三明三星食品厂的老员工,他们痛心的不是得不到改革的红利,而是他们一手创立的三明三星食品厂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名牌产品从此在三明销声匿迹……
很遗憾的是,在三明这一拔改革大潮中,三星食品、日月星啤酒、靳蛇酶(三明药厂十分紧俏的活血化瘀通络针剂)连同风云一时的“三农”一起抱团“鸣金收兵”,连厂址也没能保存,撒下了一地鸡毛,唯独三明制药厂在苟延残喘后华丽转身为而今非国有的汇天制药。这就是后话了,谁也不忍心重提谁最辉煌,但留下的历史轨迹,谁也抹除不了。至今人们还很不理解,好好的一个三星食品厂,怎么就在转型中无法摆脱“三星”(伤心)的境地?尽管各方一再努力,三明食品厂还是于1995年申请破产,从此淡出三明人的视野,有不少三明食品厂的老员工因此伤心直至,难禁热泪……但有多少人反思,却无人应答。
三明食品厂在三明人的视野中已消失20多年了,原先的厂区厂房早已被无情的铲车铲平,设备设施变成了破铜烂铁变卖,随之高岩新村一群集密的新楼拔地而起。但人们嚼到如今市面上销售的花生奶糖时,往往会让人们追忆起三明食品厂曾经销往全国各地的花生牛轧糖。老马说,曾经的三明花生牛轧糖的原材料里只放面粉、糖、麦芽糖、油,而且麦芽糖很适量,更没有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就因为纯天然,所以就非常爽口,老少皆宜。但各地中吃货,再也寻觅不到曾经花生牛轧糖的甜味和踪迹了。(图为前些年肖燕鸣(中)还乐于与老工友一聚,而今94岁高龄,已经卧床不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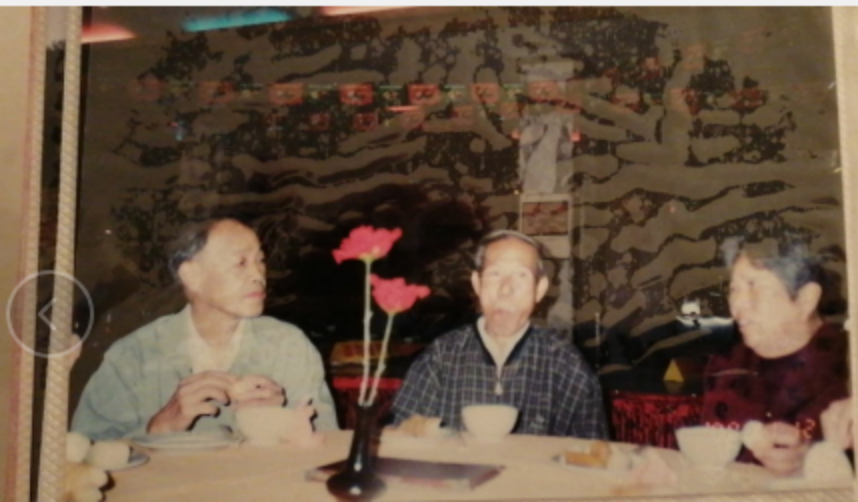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永远定格。沙溪河的后浪无疑也跟长江一样推着前浪。变迁的时代,自然变迁着三明的事物,不变的是三明人美好的心境。
2018年,马春云卖掉了原先三明食品厂房改房置换的高岩新村安置房,搬迁到了三元区省一建.西江悦楼盘窗明几亮的电梯房。老马说,虽然新购置的新楼房比仄逼、堆满杂物的安置房宽畅、敞亮多了,但依然眷恋着那片曾经挥洒过血汗的热土、入团入党隆重宣誓过的地方。
那流金的岁月,不仅仅驻留在83岁高龄的马春云心中,三明食品厂老员工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着这抹不去的记忆。
(本文作者丰烩系梅列区自由撰稿人,阿慧系市文旅系统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