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耀松
卢前校长买肉
永安的下吉山村,至今还有一条古街叫“十三行”。
这条街名的由来,是清代一个武艺高人名叫九意公,到广东广州府做笋干生意时回来后取的。他战胜了广州当地十二条好汉,称为十二行,并收为徒弟,加上自己为十三行,村人以此为荣,便把小街改为“十三行”。
清末以后,这条小街冷落寂寞了。抗战时期,福建省会从福州内迁永安县,省主席公馆、不少机关、学校等单位安置在上吉山和下吉山村的旧书院、民房和祠堂。一时间“十三行”又热闹起来,食杂店、百货店、饮食店门口,摆满卖菜担子,还有几条屠案卖肉。
1942年11月中旬,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历任国民党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卢前(又名冀野),受命为设在上吉山的国立音专校长。谁知赴任时在途经连城县金鸡岭与土匪遭遇,财物被洗劫一空,只留给他一枚国立音专的公章。他到校时衣衫褴褛,加上平时不修边幅,犹如一介寒士。

身材胖墩、下巴留一撮胡子的卢校长,生活上有两个嗜好:一是饮酒,每日至少两斤;二是爱吃猪肉,特别是五花肉。在才学方面,人称“江南才子”的卢校长,刚到永安不久,就有填词新作《永安秋夜》问世:
燕水溪,
缓缓流,
永安城外十分秋。
月如钩,
勾起心头多少愁,
潮生又潮落,
下渡照子瓜舟。
吹南管,
长夜何漫漫,
有人正倚栏。
理阙为:明月好,好月供谁看,一笑回头问吉山,山中流水几时还。山不语,水向东流去,写出愁人句,今宵没个安排处。
此歌为国立音专的保加利亚籍教授尼哥罗夫作曲,唱响永安的大专院校,后来竟风行全省各地。
这日早晨,卢前校长穿一件破旧的棉袄,由上吉山步行到十三行买肉。当屠夫切好两斤五花肉时,卢校长一摸口袋竟忘记带钱。屠夫不认识卢校长,免谈赊账,好不尴尬。
几步外食杂店的店主刘知新(省驿运处副处长黄曾樾的妹夫)认识卢校长,因卢校长曾在他的食杂店(在十三行开)内买过几次吉山老酒。平时又听人讲起卢校长是江苏省南京市人,才高八斗,不仅听过《永安秋夜》的演奏,还有“中兴鼓吹”大作问世,得到省主席刘建绪的嘉奖。刘知新见状连忙赶过去探听。
刘知新教过私塾,人面又广,他用永安方言责备屠夫:“卢先生乃是当今词曲名士,国立音专校长,你也太小气了,谁会赖你的肉钱!”
“他脸上又没写字,谁知道是校长!”屠夫不服气说。
“我先垫肉钱,连赊字也免说了!”说着叫卢校长提肉走人。
卢校长笑着迟迟不动手,经刘知新一再劝说,这才连声道谢,提着猪肉回校。
1946年,卢前先生出版了抗战八年的日记辑录《丁乙间四记》,其中一记为《上吉山典乐记》。
(黄曾樾的妹夫刘知新口述,后由其次子刘思华提供)
一张里昂旧报纸
1943年11月4日下午1时许,一批日寇飞机轰炸永安县城。桥尾、西门街、中华路、国民路、山边街和东门路一片火海,许多木头房子连片烧毁。
家住西门街的黄曾瑛逃离着火的房子时,急匆匆抱起一包东西往外跑去,惊慌中竟忘了带值钱的衣物细软。顷刻间,木房梁柱轰隆倒塌。
黄曾瑛是当时福建省驿运处副处长黄曾樾的胞妹。兄长在留学法国期间和在国内任职时寄回的书信,她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当她躲避到空旷的场坪解开包袱细看,一张旧报纸出现在眼前。
知书达礼的黄曾瑛,把报纸展开一看,顿时悲喜交集。旧报纸右上角印着兄长年轻俊拔的照片。虽不认得法文,却还记得兄长信中所言,这是一份法国的《里昂日报》。上面的文字是他获得里昂大学文学博士的论文《老子·孔子·墨子哲学对照研究》介绍,还有法兰西研究院通讯院士埃德蒙·戈布罗作的序。黄曾瑛没有抱撼损失了衣物,反为这份报纸的残存而庆幸。
山城还在熊熊烈火中,日寇惨无人道的浩劫,居民死伤的惨状骇人听闻。
入夜,黄曾瑛与从吉山赶回的丈夫刘知新一道,来到东坡兄长住处避难。兄长因公务外出,又让做妹妹的平添担心。自从兄长在法国取得建筑工程师和文学博士双学位回国后,辗转于交通部、教育部谋事、任职,抗战爆发后又随之到重庆,1942年在滇缅公路委员会秘书任上请辞,回到家乡永安受聘省驿运处。其时永安已遭日寇飞机轰炸多次,他在《抗战归里杂诗》中吟道:
为霖为雨慰苍生,
刮目当年父老情。
渐愧江湖飘泊后,
流传乡里只诗名。
三世家传万卷书,剑洲文献复谁知。百年乔木都成烬,何用伤心向蠹鱼?
她还记得年前回出生地虾蛤村时,电线杆上贴着欢迎大哥曾樾的标语:“造福桑梓,建设永安”。大哥曾樾出任县立初中校长时,把母亲60寿诞收的礼金,全部捐献作为“黄太夫人奖学金”。
没几天,黄曾樾再展看那份旧报纸时,百感交集,信手写下绝句一首并附眉批:此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报也,上有榆扬挫著文及吾小照。年前沈宜甲自法归,告越云:其法友郑重介绍读一书,视之,乃吾作。又云:彼邦作者亦常引及。闻之赧然。

无端姓字动鸡林,
廿载苔芩负愧深。
多事劫灰闽峤烬,
却留残影证伤心。
这首七言绝句,从求学法国的往事,引出近二十年来有负于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此生出诸多愤慨。国事多秋,频遭日本侵略者蹂躏,福建的山乡也难免,有旧报为见证,表达了黄曾越对家乡的热爱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图为大夫弟,黄曾樾旧居,抗战交通驿运管理处旧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黄曾樾的大妹黄曾瑛口述,已故)
吉溪畔野餐会
1942年8月,在香港中国通讯社任编辑的郑书祥,应聘校址在永安上吉山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副教授,担任史地教学工作,业余指导学生自治会文艺研究小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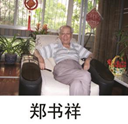
就在这期间,有个叫陈宗谷的也到这所学校学习,次年这位学生被推举为学生会研究股股长,并分别成立时事研究组、文艺研究组、民间音乐研究组和歌剧研究组。其中文艺研究组相对独立,成为进步的学生团体。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郑书祥老师,此时已隐蔽其政治身份,公开的身份便是副教授。他经常给时事组的同学作报告,对文艺组的同学提出要求:“学习鲁迅,要强调突出学习他韧性的战斗精神。”
1944年初,有的同学看到《新华日报》上刊载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那时不能公开看,郑老师提出要“扩大影响,又要有对象,审慎地传阅。”并对同学们说:“陈宗谷同学的意见很好,先介绍给有进步倾向的老师阅读,要尊重教师,团结教师,也要争取教师进步起来。”
春天来了,吉溪畔的草地上一片青绿,清澈的溪水哗哗流淌。这是1944年的初春,阳光下的北陵更显得苍郁,桔子石越发在激流冲击下如中流砥柱。文艺组的同学邀请郑书祥、缪天瑞、黄飞立等老师一道参加野餐会,师生在草地上座谈“文艺与音乐”的关系。几位老师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交流了观点,密切了师生关系。几天后,郑书祥老师调到福建省社科院工作。
谁知在吉溪畔的野餐会和座谈,被其时为临时省会所在地的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称野餐会是音专的共产党开大会。紧接着编写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墙报被撕毁,取名《铁草》的壁报有关文艺组成员写的文章被挖掉,特别是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举行鲁迅作品讨论会时,突然闯进特务分子到会监视、破坏。
在省社科院工作的郑书祥老师,在鲁迅作品讨论会被破坏后的一天,特地来到音专通知陈宗谷等学生,告诉听到的消息,省党部已列出音专10来个人的黑名单,特别要提高警惕。平时文艺组的几个同学看完《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都会用油纸包起来,藏在防空洞或旧木板地下,听到消息后又进一步作了清理。5月底,国民党特务来抓人,搜查时没有可疑的东西被搜去,终于逃过一劫。
吉溪畔的野餐会,让文艺组的同学发现,郑老师的思想观点不一般。直到5月底至6月初,音专的几位同学被捕了,郑老师还到音专与缪天瑞老师一道去找校长,要求学校出面保释被捕的同学。半年后,郑书祥老师写下三首诗以言志:
茂林喋血事犹新,避道钱塘走北闽。
欲向琴中寻正气,琴边却遇鬼逡巡。
漫说吉山秋色好,词臣杯酒看囚人。
天涯儒子心灵曲,唱彻云霄唤日轮。
莫嫌草木有飘零,便作灵均叹独醒。
野鸭纷飞冬尽讯,春临应是复葱青。
(郑书祥,永定县人,解放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资料来自陈宗谷回忆录《琴中正气》、《永安党史资料》44期)。
(本文作者裴耀松,黄曾樾的外甥女婿,岳父为刘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