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炳 烈
资深教授邓子基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也是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刚解放,他就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研读经济学。在1952年,27岁的邓子基以优异成绩从厦门大学《资本论》研究生毕业,毕业后被留校从事教学、科研,至今63载。如今,他已年逾九旬,鹤发霜染,寿眉雪白,一副饱经风霜的慈祥模样。在六十几年的风雨征程中,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将恩师王亚南“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的教诲践之于行动。先后培养了博士108人,硕士300多人,本科生数以千计;他始终不渝地倡导,并系统论证“国家分配论”,为确立该理论的主流学派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始终不渝地与时俱进,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同时,将西方“公共财政论”兼容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被学界同仁赞誉为“学术之树常青”,成为我国财政学界一棵不老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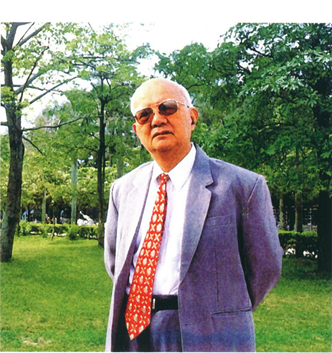
一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三明市沙县夏茂镇儒元村。在他10岁前后,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为了生计,他上山砍柴、沿街叫卖。后来到镇上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他只读过3年小学,“书到用时方恨少,事无经过不知难”,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性,他的心灵在呼唤:“我要读书!”凭着他的聪颖和勤奋,终于在1937年8月,考上了南平初中。3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福州高级中学。在校期间,他年年品学兼优,取得了甲等“清寒奖学金”,弥补了学费欠缺和生活来源的拮据。更有幸的是,他的勤奋好学精神和朴实纯真性格深深打动了当时在南平初中任教导主任的王守椿老师。王老师从心底里欣赏他,爱护他,帮助他克服种种困难,鼓励他积极向上。乃至后来将自己的侄女王若畏介绍给他,成为他的终身伴侣。成功的路上常需贵人相助,而打动贵人的,有时就是毅力和坚持。
1943年,邓子基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当时设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同时也被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录取。他先到较早开学的交大上课,几个月后,因学费不足,学业难以为继。为了继续求学,他才决定转入免学费、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就读。1947年毕业,时值国共内战,时局维艰。他先在江苏泰兴县当过税务员。后来就回本省,在罗源中学、福州厚美中学和福商中学等校任教多年。
新中国成立不久,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领衔创建成立了厦大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为了中国富强,邓子基选择经济学。1950年7月,他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资本论》研究生班深造。从此,他迈开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他心中明白,学术道路是崎岖不平的,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吃苦耐劳精神,要想攀登高峰取得成果,是难以达成的。尽管他对经济学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他还是坚持从零开始,集中精力潜心攻读《资本论》。王亚南教授要求他要明确自己的专业方向,对他说:“你曾做过税务工作,那就研究财政学吧!”为了培养邓子基的科研、教学能力,还安排他当助教,为本科生兼课。有了教学任务,以教促学,邓子基深知王校长对他寄予较高的期望值,心中充满喜悦和信心。他只有用学习成绩来回馈恩师的关怀。他更加刻苦努力,课堂、图书馆,两点一线,日夜兼程,读书、教学、思考、写文章。邓子基第一篇学术论文《苏联预算制度研究》在全国最早的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那年,他2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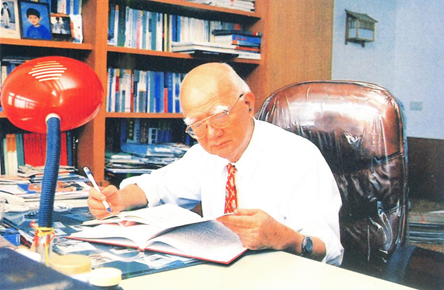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财政理论界主要流行的是照搬苏联“货币关系论”观点,缺乏理论创新。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学者就财政学研究对象问题,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的观点。年轻的邓子基对此深受启发。他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不同社会形态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简言之,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就是“国家分配论”的核心观点。1962年,邓子基发表了题为《略论财政本质》一文,文中提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并与我国财政学界前辈许廷星、许毅等教授一道参加了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论证和探讨;接着,他又发表了《财政学对象和范围》、《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等文章。对财政的本质、范畴、职能、作用、属性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证“国家分配论”。
邓子基教授为倡导、坚持和发展“国家分配论”,几乎耗费他半个世纪的心血和辛劳。多少风霜岁月,多少惊涛骇浪,他都迎难而上,奋勇向前,永不退却。然而,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财政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对“国家分配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国家分配论”是“唯心论”,是“倒立哲学”。 邓子基教授面对如此强烈的质疑,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安排他的在读研究生对几位提出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专访,虚心求教。随之,他对专访所收集到的不同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和深刻思考后,发表了《为“国家分配论”答疑》一文,文章从基本概念上指出了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同行的论点,实际上在某个侧面上和“国家分配论”有着一致性。文章还明确指出:不能把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说成是“倒立”的,是“唯心”的。通过这一学术争鸣,不仅使学界对财政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化,也使自己的财政理论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学界从西方引进“公共财政论”,主张将生产消费领域全部交给市场运作,还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过时”了。邓子基教授在归纳分析这些论点后,于1997年发表了《坚持、发展国家分配论》一文,反对完全照搬西方的“公共财政论”,认为应当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即:坚持+借鉴=整合+发展。他认为:“国家分配论”探讨财政活动的本质,是本质论;而“公共财政论”侧重于界定财政活动的范畴,并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运行过程,是现象论。因此,要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先生赞誉道:邓子基把“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巧妙融合起来,从中提炼理论,为中国财政的改革发展探索新的方法论,这需要有一种可贵的自我否定精神。邓子基教授“先坚持,后发展”的新观点,获得财政学界赞同和好评,并被写成“内参”专报中央、国务院,供高层领导作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这是对邓子基教授与时俱进学术品质和重要贡献的高度认同。

三
其实,邓子基教授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学术视野投向国际财税研究领域。1980年,他开始组织翻译出版美国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就已有涉及“公共财政”的理论阐述。当时国内财政学术界对西方主流财政理论知之甚少,这本译作与随后组织编写的《比较财政学》一书,为我国财政学界引进西方财政学开启一扇窗子。随后,邓子基教授与唐腾翔合作出版了《国际税收导论》;1989年,他与邓力平合作出版了《美国、加拿大税制改革比较研究》;1990年,他与王开国等合作出版《公债经济学》;1993年,他与巫克飞合作出版《西欧国家税制比较研究》。1990年至1993年,他主编出版《财政金融政策与宏观调控》及《财政与宏观调控》二书;同时,他还出版《现代西方财政学》、《涉外税收管理》等一批专著、教材,其中有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在研究西方财政学方面的空白。为我国改革开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财政、税收、金融管理的有益经验提供了理论来源,也起到了先行者的导向作用。
邓子基教授在财政教学和科研中,著述丰硕、自成体系。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论文起,至今已公开出版的专著、译著、教材(含合作)计75本,发表重要论文400余篇,累计2700万字。他形成了教学、科研两大著作体系,贡献突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潜心著述同时,邓子基教授还特别注重中外学术交流:1988年10月,参加法国巴黎第九大学、巴黎商业学院等单位的学术交流,并访问法国财政经济部;同年,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圣玛丽大学和纽芬兰纪念大学讲学;1990年7月,参加英国莱斯特大学学术交流,并访问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1991年10月,赴美国路易斯—克拉克州立学院出席美国第十三次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并作了《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与发展方向》的学术报告;1995 年,应邀赴日本东京一桥大学和东京财政研究会讲学;1996年12月,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讲学;等等。他还多次作为中方首席专家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专题报告,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赞誉。
邓子基教授在国内出席由部、委、办召开的高级研究会、研讨会知多少,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邓子基教授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实践中,著作等身,硕果累累。除了大量基础理论研究,还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必须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探讨,为帮助相关部门理顺关系,制定政策,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他对如何处理财政、税务、国有资产管理三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体两翼”的观点。“一体”即指以财政为主体,如飞机的机身;而“两翼”是指税务与国有资产管理就好比飞机的左右两个机翼;三位一体,三者之间有主有副,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他的这些论述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成为相关部门找准位置,制定政策的依据。
邓子基教授以辉煌的学术成就、巨大的教育贡献,无论在学术界、教育界,都得到崇高的社会威望,党、国家和社会大众都对他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蜚声中外,誉载史册。
四
邓子基教授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和培养研究生过程中,总结出一句至理名言,他说:“教师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他还说过:“人的情感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会尊敬你的。只有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促进教学相长。”
在科研进程中,邓子基教授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同行学者、专家,一贯保持虚怀若谷,求同存异,用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作出分析和评论,而不是采用怒目金刚式的反击和责难。他认为,对不同观点进行研究分析,才可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只有吸收他人积极的东西,才能巩固和壮大自己。
曾师从邓子基教授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少晖博士说,邓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在审阅学生的论文时,总要聚精会神地细读,有时为了一点研究资料或引文出处上的小问题,他要到处查证。发现哪儿论点不妥,论据不足或论述不充分时,他就做个记号,夹张纸条。让你来商量、讨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管是长篇专著,还是一般习作,他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严格审稿。这是他长期养成的治学态度和学者风范。在他办公桌上不仅有老花镜,还有放大镜,而且都不止一副。看了,令人感动。陈少晖博士还说:“我作为邓老师的学生,不仅要学习他的学问,还得向他学会做人,学会如何当个好教授。他是我心中永远的老师。”
邓教授居住的地方,离海不远,潮起潮落,听得到一阵阵优美悦耳的涛声;临窗眺望,海天一体,宽广深远,壮美恢弘,风光无限。
邓子基教授生活起居很有规律,他每天坚持看书、写字、看新闻联播;坚持散步、做操,他自编了一套适应自己活动的体操:弯弯腰,踢踢腿,这里搓搓,那里拍拍。每天练身,活络肢体,精神饱满。他一贯自奉甚薄,吃得清淡,一日三餐,以素菜为主,不沾烟酒,“幸福就是适度贫困”——邓教授喜欢这样的简单生活。
邓教授有一儿一女。但他说,他的儿女不止两个,还有许许多多。他把自己的学生都当作儿女。在学生的心目中,也都把他当成慈父来敬重。
邓子基教授执教杏坛六十几个春秋,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这其中有不少是政界出类拔萃的省部级高层领导,也有许多是财经领域的理财精英,还有才学渊博的学者、教授。但不论他们做什么,在哪里,他们在事业上有什么创新,有什么进步,都会向邓老师汇报。他们知道这是邓老师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祝愿邓老师健康长寿!
五
我长期从事财政工作,在我的同事、朋友以及领导中,有不少是邓子基教授的学生。他们常会谈论邓老师,一旦提起,都会显得很亲切的样子。我知道,凡是好的老师,不管当面或背后总是这样受尊敬的。他们之所以如此尊敬邓老师,主要就是仰慕这位大学者的人品、学识和才华。关于邓老师的许多业绩,有些是我从书报上读来的,有些就是他们告诉我的,还有下面一些事情,即是我的亲历体验和感悟。
1993年,三明市财政局组建资产评估事务所,委派我当负责人。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邓子基教授题写所名。时任局长陈良椿先生是邓老师的学生,我一说,他就赞同。于是,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先写一封信寄了去。但很久不见回音,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但就在这时,我收到邓老师寄来一封厚厚的信,信中有一张用宣纸题写的“三明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字样。笔墨饱满,苍劲有力,颇有特色。信中还附一短信,说因近月出外讲学,不在厦门,所以拖至今日,谨表歉意。我真不知道如何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说句实话,以前我对他总有一种景仰和敬畏心理,好像仰望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兴奋又胆怯。想不到,他竟是这样一位好亲近的大学者。然而,当要制铜字时,才发现多有一个“市”字,与获准的冠名不相符。删去一字简单,只是有些不舍,就将其保留下来。这块字牌一直保存到我退休后10多年。期间,这家“事务所”经过脱钩改制,更名换班,几度更迭“掌门人”。能保存那么久真不容易,这分明是对邓子基教授的一种尊敬,也正是邓子基教授的人格魅力所在。
什么是尊敬?有些地位较高的人,到哪里都成为众人的核心,领略笑脸、听美言、享美食,便自以为是受人尊敬。其实,那只是敬畏而非尊敬。尊敬是人们对一个人的品行、才能所做的肯定和赞誉。就像对邓子基教授这样的人。
记得有一年(哪年我忘了)春节过后,我陪同一位科主任到厦大邓子基教授寓所。那时,我已退休应聘在福建省注协编杂志。邓老师是本期刊的顾问,我们去拜年。说是去拜年,其实是我们想借机向邓老师当面请教一些实务工作中遇到的财经问题。我们两人都不是他的学生,更渴望获得他的“面授”。
邓教授平易近人,对我们很热情,茶几上摆了水果、甜品和炒货等,还为我们每人沏好一杯茶。他像招待朋友那样亲切,我们也就放松了心情,一边谈论资产评估的典型案例,一边享用香茶果品。邓老师认真听着,记着,还不时发问,并解答一些理论性问题。此情此景,至今不忘。
当我们要离开时,我说,很遗憾,今天没有带相机来跟邓老师照张相。邓老师说,相机有,来照。我们又回头进门来。他把一个10来岁模样的小孙子喊出来,为我们照了合影。邓老师坐中间,我们围坐在他身旁,心中充满着幸福感。
我对邓老师所知甚少。我知道,熟知邓老师的人很多,全省财税、金融系统,乃至全国财经各个领域都有。邓老师的事迹是写不完的,我们大家都来把邓老师好好写一写。
(本文作者系三明市财政局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