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 升 旗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毛泽东曾评价长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长征是被迫的,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为纪念这一重大事件,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以砥砺意志,再续新篇。
一、反“罗明路线”斗争和肃反扩大化
从1933年2月开始,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斗争。3月,又在江西苏区开展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错误的党内路线斗争,强化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的统治,打击了大批党和红军干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33年1月,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书记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随后又写了《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的意见是根据杭永岩边区斗争实际和闽西的斗争部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扩大红军问题、财政工作问题,具体反映了边区斗争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工作意见。这些报告和意见,是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抨击了“左”倾教条主义,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却把报告和意见视为反临时中央,兴师问罪。

2月15日,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已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即撤销罗明代理书记及驻永岩全权代表的工作,并“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路线”同时,还决定要严厉打击对这一路线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省委。2月20日,少共中央局也作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于是,一场反所谓“罗明路线”斗争,就在福建苏区迅猛开展起来,接着就扩展到江西省苏区,在福建、江西两个苏区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搞到每个支部,并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人人自危。
在建黎泰苏区,由于中心县委对“左”倾领导的某些指示有所抵制,也被指责建宁中心县委犯了“罗明路线”错误。建黎泰苏区划为闽赣省后,更进一步开展了对建宁中心县委的批判,并撤销中共建宁中心县委,撤销余泽鸿的书记职务,改组建、黎、泰三县县委,在基层党组织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泰宁县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退,又被认为是“罗明路线”的表现,撤销了泰宁县委书记邱光珍的职务。6月4日,调原黎川县委书记余斐接替邱光珍工作。9月,余斐又因“路线错误”被撤换。自此到1934年5月的8个月里,泰宁县委书记又先后换上了杨良生、张荷凤、肖兴余等6人。此外,区级干部调换也很频繁,如朱口区委书记钟国楚就因区委机关被大力会包围袭击而撤回县城一事被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撤销职务。因此,引起了地方干部逃跑不愿出来工作,积极的干部不敢大胆的工作甚至消沉,使闽赣工作受到损害。“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新区、边区工作只依靠上级调人,而不相信本地同志,所有泰宁县委、区委中只有两个本地干部。
“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建宁、泰宁苏区的贯彻,还表现在肃反扩大化上。建、泰苏区在肃反中,大搞肃清所谓的“AB”团、“改组派”及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抓捕和错杀了许多苏区干部,一批批干部、群众遭错误处置。“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在模范少师内大抓“AB团”、“改组派”,许多团连干部被抓起来审查,造成一时人人自危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3年春,在宁清归苏区同样展开了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共宁化中心县委书记霍步青、组织部长郑国勋被迫承认“执行‘罗明路线’”,于8月调离中心县委。霍步青后因受到政治打击,加上身患疾病,于9月病逝。随着宁清归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不断推向区乡,并把反“罗明路线”斗争当作推动工作的主要措施,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折。在开展扩红和征集粮食突击运动中,又进一步推行所谓的反机会主义和消极怠工的斗争,大量撤换、处分干部,撤销了33个突击队长和23个突击队员,“改造了8个乡主席,14个代表,3个中共党干部”。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使得宁清归干部无所适从,造成干部恐惧心理和社会的不安定,使苏区的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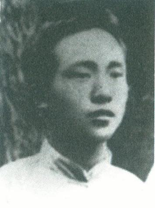
在肃反中,“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大搞逼、供、信,或轻信口供,不调查落实,轻易定案论处,造成不少错案冤案。1934年闽赣省领导机关迁驻宁化后,肃反扩大化又错误处理了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诬告、乱怀疑、逼供讯,在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恐惧,造成干部逃跑事件不断发生,给闽赣省后期斗争带来严重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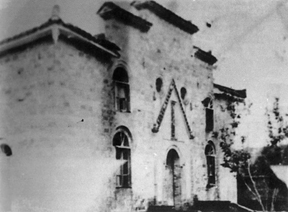
二、军事上执行冒险进攻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位于闽赣边界地区,战略地位重要的黎川。当时,负责守卫黎川的闽赣军区部队几乎全部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只剩下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兵力十分弱。在国民党军进攻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克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翼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毛泽东(此时已被剥夺军事指挥权,领导苏区经济工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黎川以南的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死守黎川。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区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于赶到黎川,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
博古、李德为了恢复“赤色黎川”,命令红军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硝石。而早在9月29日,国民党军将领陈诚即令第24师由南城进至硝石,筑垒固守。至10月上旬,国民党军第24师在硝石已构成了第一、第二线阵地,形成坚固支撑点。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10月9日开始,连攻硝石五日不克,反处于国民党军“包围的威胁之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进攻硝石的计划。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仍然命令红一方面军深入国民党军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军,并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就是拒绝战斗。”据此,红一方面军从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为恢复“赤色黎川”,御国民党军于根据地之外,连续寻战近两个月,进行了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多次战斗,不但未能恢复黎川,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入被动的境地。
11月20日,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介石的势力,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决裂,掉转枪口向蒋开火。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东南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东南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怕红军转向国民党统治区反而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国民党军后方进攻,又忽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已引起中国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内的分裂,仍然坚持其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这样,红军不仅丧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良机,而且日趋陷入不利的境地。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的主力为基础,编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前线总指挥,下辖16个师另1个旅1个团;顾祝同仍任北路军总司令,陈诚为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下辖25个师另2个旅、1个支队和3个团,两路军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

博古、李德等人被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吓倒,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进行消极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战对战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而且经常轻率地命令红军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致使中央红军不断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红军虽然毙伤俘国民党军共2626人,而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在广昌保卫战一结束,即同政治委员杨尚坤见博古、李德,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在后方的毛泽东也对广昌保卫战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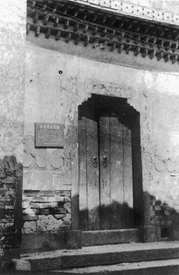
三、被迫转移——长征
经过近10个月反“围剿”作战,红军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部队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如果“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应该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有生力量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当时,博古、李德等人对此问题也有所考虑,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并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团”负责处理一切,同时把这一设想报告给共产国际。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表示“为了保存存活的力量”同意转移。但也批评博古、李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估计太悲观。因此,博古、李德等人未能果敢地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而是继续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在根据地内实行“六路分兵”,“全城抵御”,与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企图阻止国民党军的推进。又派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由湘赣革命根据地转移到闽浙皖赣边区和湘中地区,开展斗争,创建新区,吸引国民党军北上和西进,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结果为国民党军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境地。特别是9月上旬,红军在驿前以北的阵地沦陷后,国民党军“从各方面伸入到苏区大门内来,求我决战,实现其占领兴国、石城、汀州、会昌,与总攻瑞金的计划”。博古、李德等人被迫放弃根据地内部抵御国民党军的计划,决定于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去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战略反攻”。
10月6日,国民党军占领石城后,博古、李德等人决定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日,中央红军由瑞金、宁化等地出发,率领两个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8.6万余人,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至此,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格局,影响了其他各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使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由局部变为全局性的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史所未闻的伟大长征。
(作者系三明市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