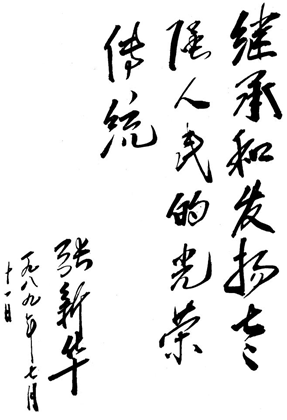■ 王 秋 燕 王 曼 玲
苦难童年
1913年5月的一天,宁化县曹坊乡滑石村药里绎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山村里,一对老实巴交的夫妇,新添了一个男婴,取名为张新华。

由于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被家人视为宝贝儿子的张新华和父母一样,一年四季很难吃得上一顿饱饭,总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贫困和饥饿伴随着每个日夜。
张新华到了上学的年龄,仍和母鸭为伴。家里就靠这群母鸭下蛋去集市换回一些油盐,再就是自家屋后坑头。坑头山上长满郁郁葱葱的竹林,还有两人都抱不拢的杉树和树叶茂盛的茶树。在张新华9岁那年,常年给地主做长工的父亲突然病倒,一卧不起。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的东西都典卖光了,天天陪伴张新华的可爱鸭子也被母亲拿到集市换了钱,再给父亲把药抓回来。可是父亲的病怎么也不见起色。不能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病死,母亲只好去借高利贷。这就等于往死坑灶跳。地主曹志国借给母亲11块大洋,约定3个月还清,曹志国怕口说无凭,立下字据,母亲将家里的竹山作了抵押。父亲还是因为缺医短药,在饥寒交迫中离世了。旧债没还,新债又来了,维系全家生活来源的竹山只好改成姓曹。
日子过不下去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只得暂时并入堂叔家。而堂叔家人口多,生活也十分艰辛。在张新华15岁那年,母子俩又搬回自己破旧的小屋。小屋年代已久,已经破旧不堪了,板壁四处钻风,晚上连灯都点不住,只要一下雨,漏得连藏身之处都找不着。好在这时候张新华已经长大了,能帮助母亲一起租种几块薄地维系生活。这时候,张新华除了和母亲下地干活,还要和母亲一起出去给米贩盐贩当挑夫、打短工。
那时,母亲像个男人一样能干,总是半夜起来做好饭装在一个草编的小袋里,再把张新华从床上叫起来,母子俩扛起扁担到离村10里地的曹坊镇,挑上一担米到百里外的长汀县,返程时,换上一担盐挑回来,往返200多里路,每趟只能挣上两毛钱。父亲劳累过度,浑身筋骨酸痛,但从不在儿子面前叫一声苦,第二天照常和儿子一道去挑担。
光荣参军
张新华19岁那年,也就是1931年冬,红十二军来到了长汀、宁化,还有一部分就驻在曹坊。这时,那些耀武扬威神气活现的老财主们却纷纷逃窜了。
红军每到一处,就深入到各个村庄,敲锣打鼓搞大规模宣传活动。一时间,村头村尾贴满了标语,还散发传单,召集大家开会。

有一天,张新华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只听见锣鼓声震天响,还听到有人喊:“开会了!开会了!”并看见一群人都跟着他们涌向村南头的大祠堂里。张新华和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跑去一看,里面比做戏时还热闹,还搭了台子,台子的四周挂满了皮袍、绸袄和一些家具杂物,像繁华的店铺一样。祠堂外的坪里都站满了黑压压的人,他们全围着红军宣传员。大坪的中间,是一筐筐粮食、一件件家具,更吸引人眼球的是一头头杀好了的肥猪,还有圈在一起叫唤的鸡、鸭。
一会儿,有个穿着灰军装的年轻的红军宣传员走上了台,他两手朝下压了压,意思是让人家安静,乱哄哄的人群立即安静下来。
“乡亲们,现在开会啦!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穷人求解放的,穷人再也不用受地主老财欺压了!今天的大会就是要把从地主老财家没收来的财产分给你们!”
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掌声,接着还有呼口号声,僻静的山村终于沸腾了!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张新华感觉脑子被红军宣传员的话语占满了,可是,还一个劲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张新华想,是啊,地主们长年不劳动,不仅吃得好,穿得暖,还要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过去,总认为穷人就是穷命,是老天注定的,现在才明白,穷人是被地主豪绅剥削压榨穷的。
“打倒地主!”
“穷人要翻身!”
散会时,人们都拿到了分来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张新华却迟迟不肯离去,他想再好好看看戏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他还想再近一点看一看那个特别会讲话的红军宣传员,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想请教他。正当他愣在那里出神时,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回头一看,正是刚才在台上讲话的那个同志。
“老乡,刚才讲话你听懂了吗?”
“懂,能懂!你讲得真好!说得我心里透亮的。”
红军宣传员笑了,并打量着他身上补丁加补丁的衣服,问他家住哪里?
张新华就指给他看。
然后,又问他家里有谁?日子过得怎样?接着便拉起了家常。那时候,他给张新华的感觉就像自家的兄弟一样,产生了亲近感。这时,又有很多人围了过来,靠近红军宣传员,他朝大家招招手,说:“乡亲们,我们都是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你们想想看,一个村上只有一两个地主,大家团结起来还怕斗不倒他们吗?我们要从他们手里分田地!”
这一席话,就像火苗落到干草堆里一样,燃起了这群热血青少年胸中的火焰,也唤醒了村里这帮穷后生起来斗争的意识。
后来,红军又两次来到村里,每次,张新华都积极带头帮助红军张贴标语,布置会场,发传单。经过红军几次宣传活动和教育帮助,村里更多的青年人觉醒了。
可是不久后,红军队伍开走了,去了长汀。临走时,红军宣传队找到了张新华,要他带领村里的青年们成立赤卫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斗争的成果。就是在台上讲话的那位红军,还特地给张新华留了一张纸条,要他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就到长汀县十字街长汀中学找红十二军的招兵委员会。
张新华不负重托,带领村里的青年成立了赤卫队,他还被选为赤卫队队长。队员们个个都是热血的、渴望光明又不怕惹祸的穷小伙。当时,大伙只觉得闹革命是一件新鲜事,至于怎么组织、怎么开展活动,谁也不清楚,只知道要团结起来和地主老财斗。于是,队员们便集中在村上地主的房子里,每天拿着梭镖、大刀、长矛、土铳等,像红军一样,出去开大会,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给穷人。
就这样,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
为了更好地把斗争坚持下去,1932年的初春,张新华和赤卫队的骨干商议,队员们暂时回到各自家里去,每天晚上集合一次,斗争不再大张旗鼓地搞了。
可不久后,反动民团开始反扑了。
有一天,张新华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噼啪枪声和洋号嗒嗒响,他睁开眼睛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落到民团手里,迅速逃进山里隐藏起来。可是,当他一骨碌爬起时,门已经被砸响了: “开门,快开门!”他让自己沉住气,从后墙的木窗里探头一望,黑乎乎的晨雾中,民团匪徒已经在屋子前后乱转,只有紧靠屋后的小山沟静悄悄的。他迅速拿起一块砖头,用力朝木窗砸去,三下两下,跳上木窗,使劲一跳,像青蛙一样越过小沟和一堵断墙,正好落到山坡上,咕噜噜地滚了几滚,便一口气跑进山腰中树林里。当他把自己隐蔽好后,还隐隐听见山下传来“冲啊!抓活的!”喊杀声,闹得整个村子鸡犬不宁。
这天清晨,张新华的母亲却遭殃了。他们没抓到张新华,便把他母亲捆起来,拖了三四里路,鲜血顺着山路淌了一地。母亲本来身体不好,哪经得住拖。匪徒一看母亲奄奄一息,以为她要死了,便扔在路旁草丛里,后来是邻居看见后将她抬回来用姜汤灌醒的。
民团匪徒们仍在村里叫嚣着要把赤卫队员活烧、活埋、剥皮、抽筋,企图以此壮势。
村子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可革命的火焰在张新华心中越烧越旺。这时,他想起了红军宣传员,并拿出一直藏在贴身衣袋里那张小纸条,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知道只有加入红军队伍,才能拿起枪杆子,和地主老财干到底,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
第二天,张新华偷偷溜回家中,和唯一的亲人母亲商量参加红军事宜。他回到家中,家乱得不能看,能砸的砸得稀烂,桌凳、坛子碎了一地,破衣烂衫扔得到处都是,吃饭的灶也被扒了。母亲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全身痛得直哼哼,让人惨不忍睹。张新华恨不能马上参加红军,拿起枪,找民团匪徒们好好清算这笔账。
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尽管就他一个儿子,心里有些不舍,但眼下这情景,知道儿子留下来,也要被这些狼心狗肺的畜生逼得走投无路,她忍着伤痛,给儿子做了一双新鞋。第二天傍晚,张新华背上母亲亲手打的小包袱和村里4个赤卫队员一起,向长汀而去。
(本文作者系军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