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升 旗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在我国杂交水稻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被国际水稻同行称为“杂交水稻之母”和中国杂交水稻救星。1981年,他成功选育出杂交水稻“明烣63”优良恢复系,并选配合适的母本,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堪称一代天骄的良种——“汕优63”,这是20世纪全球推广面积最大、栽种时间最长的杂交水稻品种。至1990年止,在全国推广面积累计9亿多亩,净增粮食600多亿公斤。被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度等周边国家引进,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亿亩。并在此后的16年连续稳居首位,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等4个全国之最。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库希博士等专家、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惊叹:“谢华安选育出这样的良种,增收如此多的粮食,杂交水稻救了大半个中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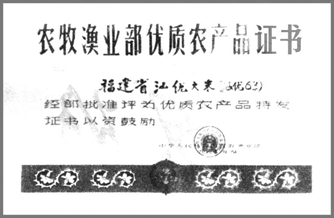
入农门,立志成为一名农学家
福建闽西是客家祖地,闽西的土楼是令全世界的建筑师叹为观止的建筑,二三百座鳞次栉比的土楼群落,组成了一幅神奇的人文景观。在这些土楼群中,有一座谢氏宜美、段美、从美三兄弟建造的土楼叫“三美楼”。 1941年农历八月二十子夜,就是在这座“三美楼”内,谢麟山的妻子林梅香降生了一颗神奇的“种子”—— 谢华安。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谢华安还在婴幼儿时期,父亲耕田,母亲上山砍柴、下地劳动都背着他。稍大一些,父母就带着他到田头地角玩耍,种地瓜、拔花生、插秧、割稻子,小华安便成了父母的好帮手。华安在田间好奇地思考着,为什么地瓜插藤?为什么花生放在地下结出果?为什么水稻穗多粒小数量多?等等,常把父母问得膛目结舌。华安刨根问底,充满好奇,在劳动中增长了知识,慢慢地对农业产生兴趣。看到父母成天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地干活,却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目睹父辈们无奈地望着因病虫侵害歉收的稻田惆怅,小华安向父母表白,长大后要学农业,做一个农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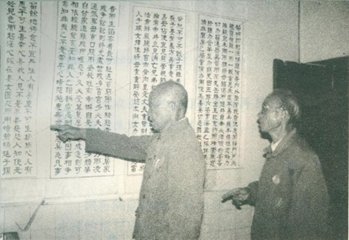

1956年夏,谢华安初中毕业,面临升学择校,在内无家财外无亲援的情况下,他只能先考虑上最省钱的学
校。当年,龙岩城里中专学校只有两所,一是农校,二是师范学校。农校不收学费,是家境困难的考生争先报考的学校。谢华安在填报志愿时考虑了两个因素,即省钱和志向,农校正合他意,他别无选择地报了农校。金秋之时,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谢华安的父母欣慰华安考上了农业学校,忘记了一天的劳累,一家人在“三美楼”内欣喜若狂,传出了阵阵欢声笑语。入学那天,林梅香这位客家女子,按客家传统习俗给华安煮了两个鸡蛋,装在碗里亲手端给儿子吃,在儿子身旁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儿子能学有所成。入学那天,谢华安与护送他的父母,挑着小木箱,翻山越岭,绕过许多小溪,越过许多坑洼,来到距家40多里的龙岩城里的龙岩农业学校,开始接受农业专业知识的教育。
在校期间,谢华安勤奋好学,读了不少农业专著,诸如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业全书》、汜胜之的《汜胜之书》等重要的农业史书与农业经典著作。还有结合农村栽种的茶叶、果树、食用菌、药材、烤烟、桑蚕等农作物栽培管理实用技术图书,课内消化老师所教,课外就阅读馆藏图书。
谢华安爱好广泛,功课也不落后,专业技能、运动水平、实践能力他都力争上游。在农校的生活中,他有许多雅好,他深知语文课对农业中专的学生走向社会很重要。文字功底是所有科学家必须具备的,小至实验结果的记录、分析,实验成果的推广应用,大至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甚至有时放松了想做农学家的必备条件,啃起了中外文学名著,通读了中国文学史,学起了逻辑修辞等等。



1956年,中国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主持会议的党的领导同志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不同性质,并批评过去对待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方式,特别声明应该把过去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大堆连锁反应式的帽子摘去。1957年3月,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杰出的生物学家谈家桢,毛泽东说:“新的遗传学要钻进去,老的遗传学钻出来,学术问题要争鸣,不要战争。”毛泽东亲自出马平息了“战火”。
一段时间,农校的遗传育种课学的是米丘林遗传学,也曾因行政命令的原因,停止开设遗传学。谢华安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谈家桢写的《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一文,心中有说不尽的狂喜,他久盼的遗传课有望开课。
1958年,遗传学开课了,学校根据专业设置的要求进行了重新编班,谢华安从307班被编到农学309班,开始接受遗传学说的教育。他读懂了孟德尔和摩尔根,掌握了分离规律、自由组合规律和连锁遗传规律的理论知识,从课堂上也认识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果树育种专家之一的遗传学家米丘林,以及米丘林学说积极倡导者李森科,辩证地看清了过去遗传学两代之间没有硝烟的无聊战争。在谢华安对遗传学知识渴求的时候,遗传学的政治问题得到了及时的化解,使他有机会认识掌握基因、染色体、DNA、性状、复制、转录、翻译、导入等等遗传学专业术语,为他以后从事水稻杂交育种科研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9年9月,谢华安以优良生的成绩毕业于龙岩农校,被分配到永安小陶农校任教(后改为永安农业中学)。这样难遂人愿的分配,使他失去了专业对口的机会,但谢华安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分配。在这所中学,他被安排担任四个班的代数课,学非所用。谢华安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原则,不论是学生的课外作业还是课堂作业全都批改,学校的师生对他的评价是有口皆碑。师生问谢华安为什么那么勤教,他回答说:“我想证明农业中学的学生也不差。”
尽管谢华安的教学得到师生的好评,但他理性地思考了自己的志向和职责,认为既然学农未能直接投身农业,就应该发挥自己学农的特长,把自己学到的农业科技知识,在农业中学里传给更多爱农的学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大胆地向校领导提出要求,教生物课。经过几番努力,校领导同意了谢华安的要求,安排他教生物课,并兼管农场的教学,谢华安终于向农业生产试验靠近了一步。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9年,学校关了门,谢华安幸免下乡却进入三明五七干校学习班。在学习班,谢华安作为一名技术员,非常同情与自己一样生活劳动的“斗、批、改”分子,接触了许多被视为“坏人”的
好人。
1972年冬,在五七干校呆了三年后,谢华安被调到他神往的三明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研、副研、副所长,1990年任所长、研究员。期间,全国正组织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科技工作者组建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他有幸被选派为福建协作组成员赴海南,开始走向杂交水稻的育种科研道路。

立梦想,让全中国人都能吃饱饭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天下第一件大事。中国是一个田少人多的国家,要解决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并非易事。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作出了坚持“三个稳定”、“两个平衡”的决策,即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粮食总产、稳定粮食库存,保持粮食总量平衡、保持粮食区间平衡。要达到稳定粮食总产的目的,需要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于是,“粮食工程”、“种子工程”便提升到国家的决策层面上来。
谢华安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他家所在的山村土瘠人穷,平常年份田里生产的粮食尚不能自给,更别说灾荒年月。父辈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求生存的艰辛,乡亲们面对因病虫侵害而颗粒无收的稻田发呆的一幕幕,连同自己打小亲历的半饥半饱的生活,给了谢华安一个永远无法驱散的黑色记忆。最让谢华安刻骨铭心的是,疼爱他的外婆在临终前,连吃一口稀饭这个小小的也是最后的愿望都没法得到满足,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像一块巨石压在谢华安心头。心酸的往事、从小的志向与国家宏观政策的亲密碰撞,擦出了谢华安全身心投入水稻育种的火花。他暗自下决心:要让父老乡亲、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吃饱饭。从此,谢华安踏上充满艰辛的求索、奋斗之路。
谢华安刚到永安农业中学任教时,曾对杂交水稻的育种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永安农校的工作条件甚为简陋,没有必备设施,他只得到50多公里外的三明地区农业局借来仪器做科研实验。1972年9月,谢华安调到三明地区农科所工作后,才正式开始了梦想中的育种生涯。
谢华安被选派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赴海南。初踏育种门槛,谢华安总想比别人多学一点,因此经常奔波在各个育种基地之间。海南聚集了全国各地数十家育种单位,但相距甚远,有的竟达几十公里之遥。在那个交通落后的年代,双脚便成为谢华安的“11路汽车”。他驾驶着他的“11路汽车”,几乎跑遍了所有兄弟单位的育种基地,锲而不舍地拜师取经。尽管人家不管饭吃,每次都得饿着肚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而且时不时还被拒之门外、一无所获,但他还是乐此不疲。

来自江西的水稻育种专家邬孝忠,非常欣赏这位同行后辈的钻研精神,毫不吝啬地从自己的育种田里拔下了一些稻苗给他进行育种试验。谢华安回福建前夕,他又从保管瓶中取出自己选育多年的15粒母本不育系种子相赠。在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科研尚处于摸索阶段,育种材料相当匮乏之时,这15粒母本不育系种子,让一无所有的谢华安欣喜欲狂。他把其中的8粒种子分给福建的同行,将剩下的7粒播在花盆里,一粒一盆,放在铁丝网内细心呵护。就是这7粒种子,让他发现了杂交水稻良种组合的途径,为日后培育一系列良种打下了基础。
在海南,谢华安和伙伴们住在最南端的崖城藤桥偏僻农村,一个仅有十几平方米的集体仓库里,陪伴他们的是无法驱除的蟑螂、老鼠。谢华安曾遇眼镜蛇,差点丢了性命。后来一位好心的大妈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主动把自己家存放棺木的房间借给了他们。小时见到棺材就感到恐怖,可此时这间存放棺材的房间却成了他们读书、写字和吃饭的地方,棺内还是他们藏书籍、宝贵资料的场所。
三四月的海南已是暑气逼人,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是一天最热的时分,也正是水稻托花授粉的关键时刻。为了观察仔细,必须守在田头。饿了,就在闷热难耐的田头吃一口面包;渴了,就喝一口自带的凉水。那种艰辛,无法形容。以田间做实验室,还常常碰到意想不到的事。育种期间,谢华安他们白天要赶禽畜、飞鸟,晚上要与危害稻种的老鼠较量。每天晚上他们都得一手打手电筒,一手持木棍竹竿,不停地驱赶老鼠。在这些方法还不奏效时,他们又千方百计地在试验田周围挖深沟放水,甚至点上马灯吓老鼠。为了种苗,他们一晚数班倒,彻夜守候在试验田头。一般农民劳作,通常是太阳出来了做工,刮风下雨收工,而育种人却不管烈日暴雨都得往田间地头跑,检查水位,担心秧苗水浅了晒死,水深了淹死。年复一年的栉风沐雨,骄阳暴晒,钢铁也会变色,人的脸不黑才怪。一到杂交授粉时,稻叶的齿就像锯子一样在谢华安他们裸露的手和手臂上锯开一道道的口子,天长日久,双手伤痕累累,皮开肉绽,先是起疙瘩,继而化脓,接着结茧,一双粗糙的手就这样“炼”成了。有一年,谢华安回家探亲,耕了一辈子田的父母竟有点不敢相认,说:“你怎么比我们还黑,你小时候也是白皙皙的。”一些农民兄弟每每握着他的手,都感到惊讶:“科学家的手怎么比我们耕田的还要粗呢?”
谢华安钟情于杂交水稻育种,由于风吹日晒、雨淋水侵,给他留下了重度风湿性关节炎;而过度劳累,生活没规律,三餐无定时,冷热不顾,又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有时胃病发作,痛得他蜷曲着身子坐在田坎站不起来,头上豆大的汗珠往外冒。严重的胃病给谢华安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有一次,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连续两次因严重胃病引起便血。那年11月发病时,正遇播期,为不耽误时间,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仍然出现在海南的田头。
水稻品种选育初期,谢华安用数百种不同材料反复进行组合试验和筛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提高,在坚持不懈中,孜孜探索积累。1975年,他和同事们培育出“矮优2号”杂交组合,试种时呈现米产优质的良种趋势,不料未及大面积生产推广,一种毁灭性的病害——稻瘟病扑面而来,枯黄的稻株整片地倒下,溃烂田中,惨不忍睹。妻子、孩子生病都没流过泪的谢华安,看到自己和同事们几年的心血被这可恶的病魔无情吞噬,忍不住泪流满面。在巨大的痛苦中,谢华安没有泄气,他和同事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总结出育种不仅要高产、质优,还要能抗病、抗虫,不抗病的杂交水稻在生产上是绝对没有前途的。他的育种生涯由此刷新:育种目标除了丰产、米质优良等经济性状外,还要具备抗病、抗虫、抗自然灾害等强抗逆性。目标选定后,谢华安马上投入艰辛的实践工作中。
早期的科研经费十分有限,为了省钱搞育种,塑料袋、塑料盘等小件物品都是反复使用,就连几毛钱的标签,谢华安也舍不得买,自己动手做竹签。当科研经费拮据甚至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谢华安和伙伴们拿出工资搞科研、办事业,这就是知识分子心忧天下、普济苍生的良知和壮怀。
1980年冬,经过无数次的杂交试验,谢华安从国内外数以百计的优良株系中,选定了一个具有抗病、强恢复力、高配合力的品系“明烣63”。“明烣63”的育成,改变了历史,成为20世纪后期经久不衰的强恢复品系。改变了中国早期杂交稻单一引用国外品种作父本的局面,同时对杂交稻更新换代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明烣63”配成的各种组合,迄今累计推广面积超过20亿亩,是应用最广、持续应用时间最长、效益最显著的恢复系。
找到了父本“明烣63”,谢华安又亲自做媒,为其选择了配对的母本——不育系“珍汕97A”株型。两者的结合,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堪称一代天骄的良种——“汕优63”。“汕优63”由于抗病性强、产量高、米质优,并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迅速风靡神州大地,1986年首登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排行榜首。全国各地好评如潮,纷纷给谢华安他们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打来喜报丰收的电报电话。“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见到谢华安,第一句话就说:“祝贺你,‘汕优63’已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稻。”农民兄弟说,杂交水稻救了大半个中国的人,这话并不浮夸,因为原产一二百斤的稻田,在引种杂交水稻后,亩数高达一二千斤。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扬言:“中国共产党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却无法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粮食总产量由建国初的1132亿公斤,增加到4925亿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10公斤增加到400多公斤,杂交水稻功不可没。此时此刻,谢华安流下了激动而幸福的泪水。
中国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说:“汕优63”救了中国杂交水稻。当时杂交水稻稻瘟病肆虐,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农民徒劳无获,欲哭无泪,积极性备受打击,科学人员心急如焚,杂交稻的推广工作举步维艰。“汕优63”横空出世,挽救了杂交水稻。据农业部统计,该品种自1986年以来连续16年种植面积居全国之冠,累计种植近12亿亩,累计增产稻谷近700亿公斤,其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和累计种植面积都创下中国稻作史之最。这个获全国第一位科技一等奖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民告别饥饿,为人类的种子工程和粮食工程作出了贡献,还年复一年地走出国门,造福异域人民。东南亚一些国家引进并大面积种植后,感叹其增产效果之显著,誉之为“东方神稻”。
在袁隆平被称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后,业内人士鉴于谢华安在育种方面的卓越贡献,亲切地以“中国杂交水稻之母”相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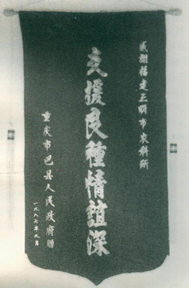
再登攀,持续创新育种科学研究
面对如潮的荣誉和掌声,谢华安没有陶醉。儿时的梦想、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鞭策着他继续努力、勇往直前。
1996年,年过半百的谢华安出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时值美国专家布郎抛出“21世纪谁将养活中国人”这一耸人听闻的论调,谢华安深感农业科技人员责任重大,提高粮食产量与质量乃是重中之重。于是,他上任伊始就积极参加了袁隆平主持的中国超级稻(稳产高产水稻)的攻关。他带领中国超级稻选育及栽培福建省课题组,先后培育出了百亩亩产800公斤的超级杂交水稻,其中“Ⅱ优明86”在云南的种植曾创下亩产1196.5公斤的世界纪录。接着,谢华安又在南方进行试验,利用头季割起后的水稻,通过施肥、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培养再生稻,这样对农民来说既省成本又省工。谢华安所培育的超级稻已连续四年实现头季、再生季亩产达到1300公斤以上,屡创再生稻的世界纪录。国家农业部由此决定,在南方推广这项日臻成熟的再生超高产水稻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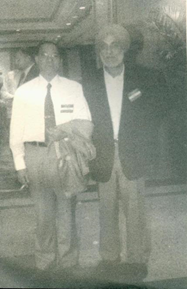
1996年,谢华安在原有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把稻种送上太空去进行育种实验的思路。经过努力,他主持的航空水稻研究走在世界前列,2002年太空稻“Ⅱ优航1号”亩产创下中国航天育种水稻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还创下世界再生稻最高纪录。
2003年,福建遭受60年一遇的大旱,尤溪县出现连续30多天超37℃高温,水稻结实率和粒重受到严重影响。但再生稻栽培的超级稻新组合“Ⅱ优航1号”仍达到百亩亩产800公斤以上的超高产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教授亲率专家验收小组进行现场验收,经田间考察、脱粒、称重、丈量面积、测定稻谷杂质及含水率等科学、严谨的环节,对该品种的耐高温性能赞叹不已。
谢华安考虑到转基因水稻是农业高新技术领域之一,也是未来水稻产业最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术项目,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抗虫基因水稻育种。国家“863”专家组鉴定认为,谢华安主持的这项研究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属国际领先水平。

欠亲情,自古忠孝难两全
谢华安生育二子一女。投身育种以来,远离家的欢乐,次子和女儿出生时,谢华安都远在天涯海角,是同事们拿着家信,告诉他又做了爸爸。女儿出生那年,老大得了麻疹,老二也被传染上,兄弟俩躺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民间说出麻疹是人脱壳,可见对患者是何等的煎熬与危险。母子四人都有生命危险,作为丈夫、父亲,谢华安真想留在家里看护照料,等妻子分娩后再走,可是,海南繁育基地育种的季节到了,育种非同一般,误一天就误一季。谢华安心急如焚,在痛苦中、在妻子的泣声中咬紧牙根,毅然踏上了南下的旅途。这第三个孩子,还是妻子自己接到人世的。1983年,已连续7年没在家过春节的谢华安,得空回家吃团圆年夜饭。当时,他的第二个孩子连续多日高烧不退,而妻舅也刚做完胃切除手术在他家休养,妻子认为谢华安这个游子这次能在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帮她一点忙。可年关未出,谢华安从电台的天气预报中得知海南低温阴雨,恶劣的天气势必影响杂交水稻父母本的生育进度,可能造成花期不遇,海南2000多亩的“汕优63”是大面积制种的一年,他心急如焚,立即就要赴海南。前脚刚踏入家门,后脚就要去海南,一向豁达贤惠的妻子第一次冲丈夫发起了火:“你在外面搞科研育种,我在家照顾父母和孩子,料理家务,你知道有多苦吗?这些年天大的困难我都是自己咬着牙撑下来,我向你发过牢骚吗?可现在,儿子连日高烧,我唯一的弟弟又胃切除,你又不是不知我爸爸就是因为胃切除而离世的,两条命都危险,你怎能无情无义,忍心走得成啊?”妻子的指责,连同病中儿子和妻舅的呻吟,像刀子一样剜着谢华安的心。但是面对事业他别无选择,谢华安硬着心肠,义无反顾地消失在妻子的汪汪泪眼中。
谢华安对杂交水稻育种像护着宠儿一样看着它们长大成熟,却不清楚自己的孩子是哪一天、哪一年突然长高长大的。他每年12月出发去海南,来年5月回家,正好横跨两个学期,根本管不到孩子。有一次谢华安回家得知大孩子学习成绩不及格,马上对他作了批评。可孩子却不服气地说:“人家的爸爸不去海南岛,我呢?谁管?”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谢华安的心。大儿子小时由于无人看护,曾从楼上摔下,至今仍有后遗症,谢华安为自己未尽到父责而深感内疚。还有一次,谢华安补偿式地讨好小女儿说:“你长这么大了,爸爸可从来没打过你。”小女儿却不“买账”,硬生生地说:“你是没空打我!”直说得谢华安急忙转过身去,怕当着孩子的面掉眼泪。
1977年农历腊月初十,是谢华安父亲61岁生日。在家排行老大的谢华安,本该全盘负责操办父亲的大寿庆典,可恰逢他试验育种基地的插秧、田灌季节,苗期管理是水稻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若回家尽人子之孝,从海南回家,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来回得半个来月。同事们知道后,特地在他父亲生日那天晚上,在橡胶林里点起了61根蜡烛,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只不过把歌词改为“祝你父亲生日快乐”。当谢华安替远方的父亲吹灭61根蜡烛时,潸潸热泪无法抑制挂上了脸颊。1997年,谢华安的父亲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要家人不要告诉谢华安,别影响他的工作,遗嘱希望儿子能为人民育出比“汕优63”更好的良种。当谢华安闻讯赶到父亲身边时,老人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母亲病时,谢华安也未能在她病床前尽孝,走时甚至无法见上最后一面。每念及此,不知多少次,谢华安默默地面对父母的遗像垂泪。谢华安这个家,是他牵挂并常使他心头涌起愧疚伤感的地方。他深感,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自己都是不合格的,在感情上亏欠着父母妻儿。然而他也知道,自古忠孝难两全,面对国家,面对广大的农民,他又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能在广阔的田野上为老百姓做点事,夫复何求!
结束语
谢华安的育种生涯从三明开始,在海南生根开花结果。由于在杂交水稻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和科研组的伙伴共获得科研成果9项,分别得到国家、省、市科技一二三等奖;他曾多次荣获全国、福建省和三明市各级政府授予的科技先进工作者、标兵、双文明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是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中华农业科技奖、王丹萍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等奖项获得者,同时也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获得者,陈嘉庚农业科学奖获得者,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然而,每每站在领奖台上,谢华安都深情地说:“这些奖章、奖金和荣誉,早已超越本身,那是党和人民的深情厚谊。荣誉再多、奖金再高也是有价的,田间地头一张张面对丰收合不拢嘴的笑脸,中国的老百姓能够吃饱饭,才是对我和所有育种人的最高奖赏。”
(本文作者系闽浙赣边区革命斗争史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