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则 慧
三明市闽剧团于1958年10月组建,1987年3月撤销,前后历时30年。
30年间,为人民服务,娱乐人民,经历了兴盛衰亡的过程。无论是繁华城市的大舞台,还是闽西北和福州沿海一带的山乡草台,都留下了他们的印迹。
1958年,为了支援重工业基地三明的文化建设,省委、福州市委十分重视,特从福州市的“善传奇”、“三赛乐”、“四赛乐”、“新赛乐”、“复兴”、“闽协”等六个戏班中抽选了颇有声誉的新老艺人黄秀清、郭韵扬、阎秋平、叶秀榕、林可清、傅生浓等56人,组成新的剧团,命名为国营三明闽剧团,由副团长黄秀清、郭韵扬带队,于当年10月7日到达三明。
到站的夜晚,三明火车站站区一片漆黑,艺人们挑着戏箱、扛着行囊下了火车,在路基边找不到站台,相互质询:这就是三明吗?
他们无法想像的是,三明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本着先建设后生活的准则和理念,在荒凉的小山城,拓展着梅列盆地沙溪河两岸,建设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城市,新来的艺人们也投入了火热的生产中。当时团部设在城关会场(现红旗影院),演职员均分散借居于工棚、民房。很快,他们自力更生,砍毛竹搭建了宿舍,居竹屋,睡竹床,生活条件相当得艰苦,但艺人们却毫无怨言。
由于剧团新组建,没有现在的剧目,更没有看家戏,艺人间也难能配合默契,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大家白天在家排练剧目,晚上下工地参加“炼钢”。他们看到了一座座土炉子“炼”出了一坨坨铁屎,以为是好钢,还乐呵呵的,边参加劳动,边演出闽剧清唱、折子戏片段。有意思的是,老艺人陈发金后来回忆说:“那时节,不少人蹲在茅坑里还背着台词。”
两个月后,剧团开始了正式演出,并分成两个演出队,一队在城区,一队年纪较轻的奔赴市郊(明溪县)巡回演出。他们徒步下乡,背包自己背,戏具自己挑,上午一场戏,下午转点,晚上再演一场。一次剧团到了明溪盖洋,农民还以为来了地质队。演出时,从没有看过戏的村民们异常惊喜,纷纷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谢意。演出队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倍感欣慰,还专程上山为伐木工人做专场表演。

翌年春,在永安、福州等地上演了《四幅锦云》、《金水桥》、《苏秦》、《穆桂英》等传统戏,旗开得胜鼓舞了演职员的情绪。继而,剧团又上演了现代戏《母亲》、《陈客嬷》等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三年困难时期,不少演职员得了水肿病,剧团照常演出,病员照样坚持。为了度过饥荒,他们垦荒三亩多的地,种了花生果蔬。在政府的关怀下,艺人们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加强艺术生产,排演了有一定质量的现代戏《胡德安》、古装戏《昙花梦》等剧目,行署副专员张恒东等亲自到现场研讨剧作、指导排练。其中《昙花梦》参加了省会演,《红色妈妈》、《打金枝》、《蔺相如》等选段参加了省青年演员会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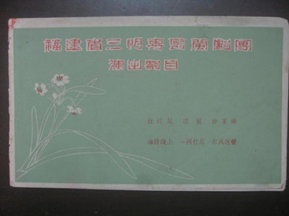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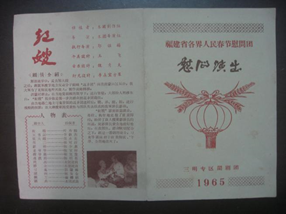
1963年3月,罗瑞卿副总理到南平视察,南平专署邀请三明专区闽剧团招待演出闽剧《芙蓉帕》,演出后,受到了罗瑞卿副总理的接见和嘉许。
当时由于外地工厂大量迁入,福州一带民工大多离开三明,语言结构复杂,观众层次起了很大变化,闽剧爱好者大大减少。于是,三明专区闽剧团第一次面临了向何处去的危机。因此,全团统一了思想,响应地委、行署的号召,毅然做出决择,改用普通话演出现代剧目,走出了新的路子。
土生土长的艺人,用“官话”演“便衣剧”,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儿。但那时的人听话,更爱听党的话。他们不信邪,没有人打退堂鼓,演员们连吃饭、行走都在练习普通话,不少艺人梦呓中吐出半生不熟的“官腔”。在短短的时间内,闽剧团破天荒上演了歌剧《江姐》,在永安影剧院连满28场,是该团难能可贵的创举。
行署专员侯林舟高度赞扬了专区闽剧团在“三大革命”(即从大城市到小山城,由古装戏到现代戏,改福州话为普通话)中所取得的成绩。
继后,又一股作气排演了《一网打尽》、《南方来信》、《前沿人家》、《红灯记》、《沙家浜》等现代剧目,在龙岩、厦门等地市扩大了影响,且又到江西赣州、广东梅县(现梅州)等地区展演,赢得了声誉。他们的目光并不短浅,为了长期生存,他们决策了以场养团,自力更生、大胆上马,建成了土木结构的东方红剧场(后改造为三明影剧院)和员工宿舍,并购置了电影放映设备。但剧场尚未待剪彩启用,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成了造反派批斗人的场所。(图为知名编剧邓超尘(右一)、梁中秋(中))

“文革”中,专区闽剧团被撤销,大部分演职员被下放明溪、清流一带农村劳动,有的退职自谋职业,一部分分配在市文工团和市内其它单位。在建团期间,地方财政总共用于补贴剧团的经费计10万多元,但该团年平均演出场次达450场以上,基本是靠自力更生生产剧目,创建了剧场。
1979年,在三明地委和行署关切下,恢复了闽剧团建制,三起三落的闽剧名丑林可清再度出任主持工作的副团长,和郭韵扬、傅生浓等老搭档重新组建了三明地区闽剧团。剧团是在落实政策中恢复的,原剧团演职员大多是在落实政策后归队的,并在三明、福州等地招收了一批年轻学员。
剧团在抓基础建设的同时,排演了《胭脂》、《穆桂英下山》、《狸猫换太子》等一批剧目,在本地和福州一带演出,反响巨大。该团还从明溪、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将乐,一路巡演到沙县,历时两个多月,建宁当时人口仅一万余的小县城,九天演出了11场,日场上座率也在九成以上。
为了更好地生存,1983年林可清转正团长,剧团重新整顿,一批冗员转岗,精干了演出队伍,排演了连台本戏《宏碧缘》、《逼反长安》等在福州、长乐、平潭、连江、罗源、宁德古田、南平等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正当人们为“戏剧危机”一筹莫展时,林可清把服务对象对准了“戴斗笠”的大众,离开城市深入到农村演出,每年演出场次均达270场以上。从1979年9月至1987年3月,该团演出收入达60余万元。
有趣的是,剧团撤销整整30年,人们在茶余饭后,依然想起三明闽剧团的著名艺人和脍炙人口的剧目。曾任多届省人大代表的邹明泉,至今还记得本文作者编的某一本剧目。1958年随团到三明的编剧邓超尘,复团后,创作了现代戏《女和尚》,仅获省现代戏会演最末的演出四等奖。后因诸多原因,他提前退休,腾出的虚位,刚好让本人进了该团。老先生在退休后,继续协助市文化局筹建市剧目创作室,培养创作新人。虽然在1995年作古,他的创作和改编的剧目,至今仍然保留着。他的一生都留给了戏剧舞台,曾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双玉蝉》,在省内外产生过影响,后被甬剧再“整理”,上了《剧本》月刊。邓老先生当年还通过省文化局长陈虹到文化部打“官司”争产权,后来无果而终。但却他在人生谢幕后的九十年代,省闽剧实验剧院将他的剧目《贻顺哥烛蒂》再度搬上舞台,进京展演,并到东南亚一带演出,颇受欢迎,这是老先生想像不到的辉煌。还是“产权”纠纷,其子邓晨曦(我省著名影视编剧)替父打著作权官司,最终完胜,获6万元稿酬。
文中提到先行者黄秀清,是享有盛誉的老生,复团时年事已高;郭韵扬复团时老当益壮,继续扮演老武生,还导演过连台本戏《顾青云》,1983年后退二线;傅生浓,复团后着重导演工作,执导过本人创作的历史剧《曲江怨》、《龙凤双飞》、《千金买骨》、现代戏《分家》等,曾任省人大代表,为国家二级导演;叶秀榕,复团后先期饰演花旦、刀马旦,任副团长,后在二线培养新秀,执导过本人改编的古装戏《康王告状》,由省电视台录制热播多年。为国家二级演员,第一届三明市人大常委。
最值得一提的是名丑林可清。人还在舞台上展示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有多神奇,一旦到了追忆,才感受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多么难得的瞬间。
笔者是自1971年始从文艺舞台上滚过来的,看过很多的戏,也跟很多的演员、导演合作过,唯独没有其时三明市闽剧团的闽剧名丑林可清印象深刻。提起林可清,大多人亲切称他“一可”,老三明的戏迷还是留存着很深的记忆。我记得当年三明闽剧团排演的《母子恨》(既传统名剧《咬奶头》),在三明、福州城乡至少有演过不下500多个场次。他是曾经的右派,被贬黜到三明剧团,又是后来的三明市第一届政协常委、民盟省委委员、剧团团长,经历了三起三落的磨砺。他与其妻子阎秋萍搭档,主演一个不成器的烂仔卞希人,从小偷小摸到江洋大盗,阎秋萍扮演溺爱孩子、怂恿逆子的母亲,最终在法场上,被钟爱的儿子临刑前咬断乳头。可说演到哪儿,红到哪儿。当年只要我跟团,一可非逼着我在台下看戏,哪怕是一看再看。看着看着,后来我还真看出了名堂。很多演员在他们演的老剧目中,那一招一式,一唱一吟,从不走样。一可却不是,《母子恨》一演再演,他没有像老油条一样被炸得没感觉,他没有一场重样,他的一颦一笑,一说一唱,从不跟前一场“雷同”,都给观众一种重酿过的艺术感受。《徐九经升官记》他扮演一号主角徐九经,也是即兴表演,场上每每翻新,即便主要唱段,叠唱72个“官”,有严格音节伴奏,他也娓娓动听地变幻着唱词起承转合,他的情感在演绎中不断出新。《徐》剧大概也演过300多场,他的角色,从未固定过演出模式。
我曾跟圈内人士探讨过,一可“没”派?有说,老可就是靠爹妈给的那逼脸面、声腔,喝的是“天水”;有人说,一可就是一可,他与旧戏班到1953年戏改后的闽剧名丑都不尽相同,因为有他的个性;有人说,闽剧的“三花”脸(即丑)有什么派不派的,能逗乐就行。
后来的1987年,三明市闽剧团在鼎盛时期却撤销了,三明的名人,就因剧团没了,他的政协常委也随之“退役”了。两年后,不到60岁的一可不甘寂寞,也因为他戏心不死,居然下海创办起了民间职业剧团,1990年笔者还在《中国文化报》二版头条报道了他是福州沿海第一吃“螃蟹”创办民间职业剧团的艺人。可惜他只经受了两三年的风浪,便急流勇退了。
尽管在剧团时,笔者虽然被一可多次“修理”过,但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我们还是握手言和,没有了剧团,我们还常常研讨舞台艺术,尤其是在修《福州闽剧志》中三明部分时,多次研讨剧目和艺人的得失,唯独他很少谈及自己的成就。
1993年,他胃癌手术后不到六个月就悄然离去。在世时,一可曾经多次与我调侃他走时有多少个花圈。他哀叹道:我看最多六七个,人情薄如纸啊。谁也使料不到,他走后,有43个花圈,41部车子,500余人上山相送,三明市政协、市委组织部、民盟福建省委等单位都送了花圈,并派官员参加了追悼会,这是文化系统迄今为止最热闹的一次。
到了2000年,笔者参加全国首届中青年剧作家研修班,名师授课讲到了梅派,笔者对一可多年谜团终于开解。老师说:梅派为什么居四大名旦之首?就是因为它雍容典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非常中庸,它最适合刚学戏的人入门。但别看它易学,却相当的难,就是你想要上层次很难很难。许多人说梅派是“没”派,就是因为它的特点就是没特点。那就是一种大气,是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我想,这也是对闽剧名丑林可清的艺术评介与演艺的诠释。
(本文作者系三明市剧目创作室退休干部)